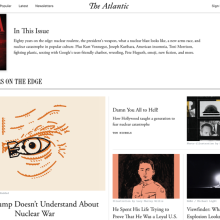编者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全球化大变局的冲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保持对地缘政治博弈和金融安全博弈的充分敏感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思考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需要拉到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来寻找时代所处的坐标。现代全球化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十九世纪末到一战之前是全球化第一波浪潮,建立在英国霸权和西方列强扩张的基础之上;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全球化的政治基础走向了崩溃和重构;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治理体系成为了全球秩序的基础,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寻求独立自主发展;冷战期间,美苏争霸和两大阵营的对抗是一个斗而不破的过程,这一阶段新一轮的全球化开始孕育;冷战结束之后,国际体系进入一超多强结构,新一轮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体现在全球供应链崛起、产品内分工深化与金融全球化扩张。
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一波全球化浪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已进入新一轮全球化大变局,全球化的地缘政治基础和在主要大国的国内政治基础都面临重大挑战,全球化面临重组的压力。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地缘政治与安全格局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更迭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是最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但随着十八世纪末法国入侵荷兰,阿姆斯特丹走向衰落。英国和法国,特别是英国,替代了荷兰的国际金融主导权。
十九世纪国际金融中心演变的主线是伦敦和巴黎的竞争。由于法国在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中陆续失败,巴黎与伦敦的差距日益扩大,走向相对衰落。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伦敦是主导性的全球金融中心。后来随着美国的崛起,经历了冷战及其后的新一轮全球化,纽约替代伦敦成为了最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而伦敦得益于离岸美元市场的发展,依然保持着重要地位,形成纽约—伦敦双中心的架构。

伦敦金融城
(图源:英国独立报)
1980年代以来,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推进,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逐渐形成了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发展的新格局。
在全球化大变局的背景下,经济金融政策不仅要考虑经济理性和发展的逻辑,也要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和安全的逻辑,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可能脱离国家金融实力和金融安全的宏观基础。国家金融实力取决于很多维度,包括实体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深度、广度和韧性,外交关系网络、军事力量和辐射范围,以及治理体系的有效性等。
从体量上看,2020年,中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占到全球GDP的18%,贸易占比是全球的12%,已经超过美国。然而,人民币占全球外汇储备比例只有约2.3%。美国虽然只占有11%的全球贸易,但是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金字塔结构,是在美元和美国金融霸权主导下的高度不对称、不均等体系。
国际金融博弈有很多层次,既有双边关系上的博弈,包括金融制裁和援助,也有多边结构上的博弈,包括通过主导多边秩序、规则来塑造体系运作,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博弈,包括对金融监管理念、改革思潮的影响等。当前,在所有这些层次上,国际金融政治化、武器化的趋势都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关注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代表着一国金融体系抵御内外部冲击的能力,代表着金融主权相对处于一个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国家利益处于免受金融手段和渠道威胁的状态。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十大报告充分强调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重要性。我们在思考如何巩固和增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需要有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局出发,充分把握香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独特战略地位和角色。一方面,香港应进一步发挥“双循环”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在全球产业链重组、地缘政治变局、产业技术革新的背景下,聚焦 “一带一路”,引导金融市场更好地配合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和发展。另一方面,香港应进一步融入内循环,推动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也推动金融业更好服务本土实体经济和创新。此外,香港在建设与国际接轨且安全可控的金融基础设施方面,应当发挥引领作用,包括充分推动金融科技及金融监管科技创新,把握数字货币和支付技术革命的机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涉外金融基础设施的自主安全可控水平。

图源:AFP/Getty Images
面对全球化大变局的冲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保持对地缘政治博弈和金融安全博弈的充分敏感性。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最理想的情况是事前化解风险,但也需要进一步建设金融安全的事中、事后反应机制,做好应对极端状况的准备。
(本文内容原载于《紫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