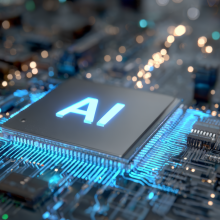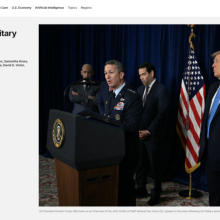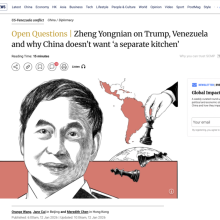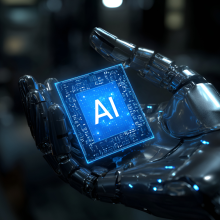编者按:5月20日,中国与东盟十国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作为两大发展中经济体,中国与东盟有望通过自贸区3.0版建设共同扩大相互开放,全面扩展新兴领域和新质生产力合作,将为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超大市场提供重要制度性保障,为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双方共同繁荣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东盟自贸区正逐渐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之一。本文深入剖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与深层挑战,指出当前贸易增长既受益于协定红利与消费升级,也受到“转运贸易”等因素影响。作者敏锐地指出,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市场”面临劳动力、资本流动限制及政治意愿不足等结构性难题,尤其是公众对经济合作的政治担忧已成为关键制约。文章突破传统经济视角,强调政治互信与利益平衡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产业实质性转移、风险共担与双向消费促进等务实路径,为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兼具战略性与操作性的思考方向。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现状与前景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和邀请,我想主要谈谈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景的问题。
正如其他嘉宾所言,自由贸易区和我们通常理解的贸易一体化其实有很大区别。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尤其是在2020年,东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种贸易额的增长,一方面明显反映了中国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累积效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国内消费的提升,特别是对来自东南亚的农产品需求增加。这两点共同推动了双方贸易额的大幅增长。
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以来,出现了所谓的“转运效应”——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通过越南,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转运,以规避针对中国的关税。而现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任期,明显有意堵住这些漏洞。因此,在今年或明年,我们可能会看到针对转运的关税对中国与东南亚双边贸易的具体影响。这点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
二、自由贸易协定背后的政策与政治因素
接下来,我想重点谈谈自由贸易协定(FTA)背后的政治因素,探讨如何推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更深入的经济和贸易一体化。“共同市场”这一概念与单纯的自由贸易协定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在欧洲的语境中,共同市场不仅意味着货物自由流通,更强调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生产方式的深度融合。这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来说,是一个非常高层次的目标。即使是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内部,也尚未真正实现共同市场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谈论中国—东盟共同市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稍显遥远的目标。
然而,与此同时,当我们考虑中国与东南亚在政治合作上面临的问题时,我认为许多问题都关系到实现这种共同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例如,资本流动性问题。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在资本流动方面有诸多限制,而许多东盟国家对跨境资本流动同样设有限制。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流动。东盟内部实际上并没有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这意味着人们很难轻易从东南亚一个国家移居或工作到另一个国家,而自由移居是欧洲自由流动劳动力模式的核心。
而在中国—东南亚关系的背景下,虽然中国(大陆)最近对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放宽签证政策,但总体来看,中国(大陆)的移民政策依然非常严格,特别是针对那些拥有大量劳动力剩余的东南亚国家。例如,在香港和新加坡,有大量来自东南亚的家庭帮工和外来劳工,但中国(大陆)政府对于外来劳工进入市场一直采取严格限制和管控,这是因为大陆自身保有大量的劳动力,政府需要保护国内就业市场。所以,像劳动力自由流动这样的问题,在当前环境下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困难的。
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在考虑与中国进一步的经济一体化时,许多公众关切并不完全是经济层面因素,更多是针对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潜在政治影响。举个例子,基于我自己关于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的研究,我们在几个东南亚国家做过民意调查。以泰国为例,公众总体上对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对中国移民的态度却普遍非常负面。因此,在许多东南亚国家,涉及中国人前往东南亚工作或居住的流动性问题,都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例如,印尼在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合作、高铁建设及其他项目谈判时,其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劳工的使用——印尼国内对这些项目中大量使用中国劳工的反弹非常大。这说明,当我们谈论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时,许多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所以,当我们谈论未来实现共同市场这一远景目标时,实际上很多问题并非纯粹经济层面的,更多的是政治层面的。
经验地看,欧洲在二战后建立共同市场并非完全出于经济必要,而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需求,旨在实现战后西欧的政治和解,尤其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德国与法国需要克服历史恩怨和政治分歧,达成和解。这种政治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关键因素。同样地,如果我们思考中国与东南亚未来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政治意愿和政治合作的重要性可能远超过纯经济考量。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在政治意愿上确实存在不少障碍,阻碍双方进一步合作。首先,即使我们谈论东盟的统一,但在面对中国问题时,东南亚各国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各种民意调查以及来自新加坡的民调,我们可以看到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对中国持较为积极的看法,马来西亚和泰国处于中间立场,而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则较为负面。这种对中国的政治态度差异导致在政治层面的合作中很难形成统一且持续的立场。此外,东盟现有的共识机制意味着任何成员国都拥有否决权,多样化的政治观点使得达成一致变得尤为困难,这可以说是当前东盟与中国合作中的一个主要政治障碍。
三、中国—东盟建立共同市场的可行路径
那么,在面对这些政治难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能做些什么?虽然共同市场是一个长期的未来目标,但或许我们可以先从短期着手,寻找提升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可行路径。我认为,首先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过去几年中国对东南亚的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转运”模式。许多中国企业将产品运到东南亚,在当地进行一些非常基础的简单加工,但这意味着东南亚经济所获得的附加值其实并不高。因此,进一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一个关键点,可能就是需要中国部分产业的真正转移和落地到东南亚地区。
刚才的讨论中提到了日本的战略——将供应链和投资分散到东南亚,真正把东南亚打造为其许多产品的生产中心。以泰国为例,其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国之一得益于冷战时期日本把泰国作为其汽车生产的核心基地。同理,现在中国面临美国的关税压力,而美国方面也会严防关税漏洞被利用。因此,中国必须真正把部分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不过,这样的转移需要中国国内做更多的准备和调整,才能顺利推进。首先,需要加强关于东南亚的了解,光说“大家应该多了解东南亚,加强人文交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企业进行系统性的教育,让他们真正了解东南亚的挑战与机遇,知道如何有效地投资。企业“走出去”说起来很容易,但如何规避投资东南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陷阱和风险,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趣的课题。
最近,我们在中国做了一项关于东南亚认知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对东南亚的危险感知非常高——缅甸被评为最危险的国家,泰国也因为近期媒体的关注,被很多中国民众视为高风险地区。这意味着,即使是在个人层面,投资东南亚的政治意愿也并不强烈,大家担心被绑架或公共安全问题等。因此,我认为中国需要与东南亚加强合作,在执法和其他相关领域共同努力,改善中国公众对东南亚的整体印象,从而提升投资和交流的信心。
其次,显然还需要建立共同的政治意愿,尤其是要缓解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可能会将大量产品倾销到东南亚,导致当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多地提升国内消费,一方面是促进对“中国制造”产品的消费,另一方面也要增加对东南亚产品的进口和消费,这样才能实现双赢的局面,而不是让中国单方面获益。实际上,东南亚很多抱怨的根源就在于许多合作最终主要让中国受益,而东南亚的利益未能充分实现。我认为,中国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应有这样的政治意愿,共同制定策略,确保中国获益的同时,东南亚国家也能获得公平的利益。
*本文系作者在由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合办的“第三届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高水平开放与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上的发言整理。
GBA Review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