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去的2024年被世界气象组织认定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在《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COP30召开之际,全球气候治理如何在“高温警报”与大国博弈交织中走出困局,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追问。
本文以COP30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当前气候治理的三大新动向:一是气候议题高度政治化,深陷党争与民粹裹挟;二是多机制并存下的治理碎片化加剧“制度停滞”;三是俄乌冲突、北极开发等地缘热点外溢,重塑减排与能源版图。在此基础上,文章聚焦美国“开倒车”、欧洲“言行不一”和“全球南方”话语权上升的格局变化,提出中国应顺势而上,在多层级治理、稳健落实“国家自主贡献(NDCs)”、勇于担当关键角色等方面拿出更具引领性的行动方案。
引言
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研究表明,2024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其平均地表温度较1850-1900年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55°C(±0.13°C)。《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是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不超过2°C,并努力控制在1.5°C以下。虽然气候变化的判断应基于长期趋势而非单一年份的波动,但相关研究指出,2024年的极端升温是一个强烈而警示性的信号,显示全球变暖不仅仍在持续,甚至可能正在加速偏离1.5°C路径。与此同时,2015-2024年被确认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趋势的系统性与累积性。
在此背景下,如何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切实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紧迫议题。本文将以在巴西召开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为中心,重点探讨全球气候治理的最新动向,并向相关决策部门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全球气候治理新动向
1. 节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与COP30
2025年11月10日,UNFCCC的缔约各国代表在公约生效三十余载 后再次来到巴西,在巴西贝伦市举行COP30(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直译为“缔约方大会”,一般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本次COP也恰逢框架中重要的协议——《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的时间节点。如前所述,在《巴黎协定》中,缔约方们设置了“2°C与1.5°C路线”,并确立了“国家自主贡献(NDCs)”减排、每五年更新、接受透明度审查的机制。但多项报告指出,即便目前提交的NDCs正在更新,但如果继续按当前轨道执行,全球升温仍可能达到约2.3°C–2.8°C,而非1.5°C或2°C。
在COP30开幕致辞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执行秘书强调称,虽然排放曲线“首次出现下降趋势”,但必须“远远加速”才能达成目标。与会各方将焦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融资”的大额目标上,试图推动到2035年每年“整体气候融资”规模达到约1.3万亿美元,同时还特别呼吁将“适应资金”交付规模至少提升至当前水平的三倍以上。在聚焦如何“将雄心转化为现实”的同时,大会还提出了“多层级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的概念与倡议,即强调地方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协作。
大会最终通过名为“Global Mutirão(全球动员)”的决议,汇集了多个议题(减排、适应、融资、贸易-气候连结等)以“动员大全球”为主题。同时,大会还发布了Global Climate Action Agenda(全球气候行动议程)的最新报告,收集了超700项案例、570个“解决方案数据库”,举办了约350场活动,强化社会、地方政府、非国家主体在气候行动中的角色。大会完成了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的第三次审查,进一步明确“损失与损害(Loss & Damage)”支持机制的运作框架。
尽管有上述成果,但关键问题如化石燃料退出路径、全球统一碳市场机制、明确提升减排目标等并未在文本中获得强制性承诺。例如,在COP30的最终文本中,明确地停止新化石燃料投资或按时间表逐步淘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承诺并没有出现,而至少29个国家原本将此设为红线。
2. 主要区域与国家立场的新变化
美国
特朗普(共和党)政府自2025年1月上台后对美国气候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逆转了此前拜登(民主党)政府“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重新加入《巴黎协定》、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相较于2005年减少50%-52%、2035年相对减少约61%-66%、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且在政策上大力支持清洁产业发展等),就职首日即再次启动退出《巴黎协定》,并签署行政令“在国际环境协议中美国优先”,明确美国在发展经济和能源生产方面优先于国际环保协议。同时,特朗普大规模削减或暂停绿色项目补贴、太阳能风电税收优惠、环境正义拨款等,强调化石燃料(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和核能的发展。除退出《巴黎协定》外,美国政府还冻结或重新评估气候融资计划、停止或缩减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相关援助。并且随着特朗普政府再度上台,废除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推出新的反气候政策的行动也在陆续进行中。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本次缺席COP30,但有两位民主党州长——加州的加文和新墨西哥州的米歇尔出席了COP30大会,并对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同时,加州也和巴西Pará州达成了气候合作备忘录,共同在森林火灾预防、绿色港口、低碳运输燃料、学术交流等领域开展协作,呼应了COP30大会提出的“多层级合作”倡议。由此也可见美国联邦制度中的地方-国家张力。
欧洲
欧盟已立法确认,到203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应至少比1990年减少55%。同时,欧盟还提出了一个长远目标,即到2040年拟达到约90%减排(相较1990年水平)以迈向2050年气候中和(净零排放)。
欧盟国家、区域向来是“气候正义”话语的强力领导者,但研究指出欧盟在实践中存在“言行不一”的矛盾。有分析指出,尽管欧盟在谈判中强调全球气候公平,但其内部政策、制度优先级正向经济竞争、产业保护转移,弱化了对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转型成本支持的力度。同时,其内部也面临挑战: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产业竞争等现象,以及右翼政党的上升,使得部分国家和政治力量对脱碳政策、绿色税收、产业脱碳转型成本的抵触升高——表现为在“气候领导”话语上强,但在“行动落实、国内外支援、产业脱碳”上有所下降。比如在2040年减排目标谈判中,有批评者指出欧盟可能倾向于借助碳信用、国际补偿机制来达到目标,而不是大规模国内减排,从而削弱气候正义原则。研究指出,这正影响欧盟在气候公平/气候正义定位上的可信度。
多数欧洲寄生于极右/右翼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政党对气候政策持怀疑或反对态度:他们往往质疑“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主要致因”,并且反对“精英主导”的绿色转型议程。与目前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共和党政府一样,这些政党倾向于强调“国家主权”、“经济/能源安全”和“反欧盟干预”等主题,将气候议题与移民、全球化、精英主义批判等捆绑,从而把气候政策塑造成“精英议题”或“外部强加的议题”。所以,当右翼政党主导或影响政府时,可能使政府优先考虑经济增长、产业竞争与国家主权,而非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补偿和历史责任(如积累碳排放)等。但这也会相对应地提升如中国、“全球南方”等国家、区域在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
“全球南方”国家
“全球南方”国家长期以来被视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群体,它们虽然在历史上排放较少温室气体,但却更易遭受气候冲击(如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粮食/水资源压力等)。但另一方面,全球南方也正在从“谈判中的被动方”转向“规则参与者/塑造者”——以印度为例,在早期气候谈判中主要处于典型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强调发展权、减排成本及外部资助等,被动参与国际机制。但近年来,印度转向主动塑造气候治理规则体系:如南北国家在太阳能领域合作的平台国际太阳能联盟(ISA)就是由印度提出并牵头成立。在COP30召开前夕,印度也明确、积极呼吁一个“公平、可预见、优惠的气候融资”,强调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责。
南非也是全球南方中主动塑造气候话语的典例。南非通过《气候变化法案(Climate Change Act 2024)》把减排和适应机制法制化。在本年度即将召开的G20峰会中,南非将作为主席国,并把气候融资、债务减免和可持续能源转型设为议程重点。在本次COP30前,南非也提交了新的NDC,并强调“损失与损害”“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等议题。
总体而言,全球南方国家正呈现出从“要求资助、强调自身发展权”转型为“参与话语建构、规定与制度设计”的角色改变。
二、对新动向的研究与判断
1. 气候议题政治化
气候变化及其相关技术、工程本质上从属于科学和工程范畴,但由于在资本主义模式下,自然系统被视为低成本的资源来源,同时环境破坏的后果被排除在市场机制之外——如果气候危机根源在于经济-制度结构(如资本积累逻辑、能源体系、产业结构),那么单靠技术或市场自发机制往往难以根本转变。如有研究指出,“气候正义是政治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
当气候问题不再只是科学或工程问题,而触及“谁减少排放”、“谁承担成本”、“谁受益/谁受损”和“谁制定规则”等这些权力分配与制度设计问题时,就自然进入政治范畴。正如耶鲁大学研究者指出:“气候变化在(西方)民主体系中成为政治问题,原因包括选举周期短、党派身份强、公众意见被党派化。”同时,也有研究称“数据显示自1990年代起,美国气候环境态度高度极化,保守派群体的环保态度下降是主要驱动之一”。
2. 治理机制碎片化
在传统全球治理理论中,我们设想可以由一个中心化的权威(例如UNFCCC机构)来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然而,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主权优先、气候问题的复杂性、气候行动主体的多元化、多机制并行和利益竞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了“碎片化”的形态——在一个气候议题下,多个治理中心、多种制度和多元主体各自运作、重叠甚至冲突。多中心或去中心化的全球治理也许并非必然负面,但“冲突性的碎片化”可能会削弱治理效能与治理的合法性。
除了UNFCCC及巴黎协定外,世界范围内还存在有很多其他的区域、多边和双边气候协议,气候“俱乐部”,技术合作网络和企业、金融为主体的机制。不同机制可能在碳定价、技术转让、绿色金融、“损失与损害(Loss & Damage)”等方面交叉运行,导致责任、标准、监督主体不清,同时挑战了以国家为主体、以谈判为中心的传统治理模式,使治理行动呈现向“地方政府+城市+企业+金融机构”赋权的趋势。
以近期国际海事组织(IMO)在推进海运温室气体减排框架上的延期为例,即使是一个全球性的制度机制,也可能因国家利益分歧、技术准备不足、产业压力大等因素而偏离统一的轨道。
3. 地缘政治热点的外溢效应
一项2024年的研究显示,过去两年俄罗斯-乌克兰军事冲突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了全球175个国家一整年的排放量,在此之外还带来了能源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供应中断、森林与土壤遭破坏和污染(包括放射性沾染)扩散等环境灾害。
不过由于俄乌冲突带来的政治经济效应影响了欧洲等区域的化石能源供给,反而在能源治理方面向可持续发展加速前进——加快了欧洲许多国家对化石燃料替代路径(或延缓转型路径)的决策,从而影响气候减排的政策空间。然而,显示欧洲能源结构张力的是,因为俄气缺位和美国保守化的综合叠加,美国近期正试图通过与波兰等国合作,向欧洲(特别是乌克兰)出口美国产液化天然气(LNG)。
北极地区的战略资源开发目前也是地缘政治热点之一。目前,北极地区的冰层正因气候变暖而加速消融,新的航道被开放,资源(如稀土、矿产)开发热潮上升。多个国家在北极海域拥有沿岸优势,如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岛)等,因此资源开发与航道控制往往与国家安全、军事布局紧密相关。虽然目前存在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这一多边机制,但其聚焦环境、科研合作领域,不具备安全职能。
如北极理事会的一项报告中指出:“(北极地区的)矿业扩张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原住民族社区、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并建议所有在北极进行的开发活动“应将生物多样性目标纳入规划与运营阶段,包括油气、运输、旅业、矿业”。理事会还曾指出,俄罗斯北极区油田的伴生石油气放焚量巨大,并向俄罗斯提出应用某种技术以降低排放量的建议。科学评估、技术建议、最佳实践倡议等非规范性文件是北极理事会目前唯一的“治理”形式,缺乏政治上的约束力。
4. 对COP30影响的综合判断
以上新动向叠加后产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停滞(Gridlock)”,即目前对全球治理的要求使得所有国家互相之间“深度依存(Interdependence)”,处处需要合作却处处难以合作,因为旧有的治理机制、规则、行政体系不能有效应对,于是合作谈判停滞、制度改革缺乏执行力。
从本次COP30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仍有强力的证据支持这一全球治理“停滞”理论——一个“高开低走”的气候变化大会。原本应该将全球气候行动的雄心落实到行动当中去的COP30,然而最后却以一个空洞的文本结束。化石燃料出口国或能源依赖型国家担心退出化石燃料会削弱其经济或国家利益,因此不愿接受强制退出机制。据报道称,沙特、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就化石燃料退出的话语提出强烈反对。
三、政策建议
1. 积极响应COP30“多层级治理”倡议
有研究指出,在全球治理中,传统的国家间多边机制常常因为国家利益分歧而陷入“停滞”,而引入城市/地方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等非国家主体,将有利于增强治理的弹性和制度的可执行能力,从而打破“停滞”。
我国已有“从中央到地方”的落实机制和责任体系,在气候治理中,我国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执行任务。然而,虽然制度体系存在,但层级之间、跨部门的协调仍有脱节。有研究指出,我国很多气候政策虽然密度较高,但强度和落实效果有局限。
因此,在现有的制度基础上,应当赋权非国家主体,探索一条主体多元化的气候治理模式。
2. 稳健落实、推进、完善NDC
较多报告、论文已经指出,以人类目前的减排进度为基准进行预测,我们甚至不足以完成《巴黎协定》的最低目标。
目前,我国已向UNFCCC提交了最新的NDC(203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峰值减少7-10%),但据气候研究与行动倡导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CAT)评估,与理想模型相对比,我国的NDC距离理想状态仍有较大差距。
我国的国情确实决定了在探索绿色转型时必须兼顾气候正义与转型正义——即如何在保障十几亿人口的生存与合理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绿色、低碳的能源和经济转型。所以,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优的路径,亟待解决。
3. 勇于担当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角色
在美国“开倒车”缺位、欧洲陷于内困和“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提升的今天,世界的目光已在寻找新的锚点,并逐渐聚焦于我国。我国应当通过先进的、有领衔力量的气候话语和切实、有效的气候行动,把握住这一新动向带来的机遇,再次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与地位,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首先,我们可以效仿巴西,与美国“蓝州”进行接触,在气候政策等方面达成合作协议、备忘录等;其次,可与欧盟、欧洲国家进行谈判,化解不合理的“气候壁垒”,加强新能源产业的合作,共同参与气候议题建设;再者,应当在与我国无直接关系的地缘政治热点中继续保持中立,倡议和平,息战止战,不仅可以控制战争的大量污染排放,也可以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最后,可以将气候变化的议题与我国的国民教育体系深度融合,以响应COP30对“新职业”的倡议,在新一代学生中培养出认可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热爱家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氛围。
GBA Review 新传媒
评论文章
 今日伊朗,明日古巴?特朗普的“第三目标”|GBA编译
今日伊朗,明日古巴?特朗普的“第三目标”|GBA编译 袁太平、朱静慧:巴阿边境冲突对出海央企国际经营战略版图拓展的影响分析与建议
袁太平、朱静慧:巴阿边境冲突对出海央企国际经营战略版图拓展的影响分析与建议 评兰德公司报告: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竞争本质是“社会竞争力” | 科技观察
评兰德公司报告: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竞争本质是“社会竞争力” | 科技观察 周承哲:凯文·沃什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逻辑的“体制性调整”|全球改革观察
周承哲:凯文·沃什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逻辑的“体制性调整”|全球改革观察 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引发跨区域反击行动 | 全球地缘政经动态(2026年第4期)
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引发跨区域反击行动 | 全球地缘政经动态(2026年第4期) 对话郑永年:美国2小时斩首哈梅内伊,中国还要让AI只做“烟花”吗?
对话郑永年:美国2小时斩首哈梅内伊,中国还要让AI只做“烟花”吗? 美国对伊“终极方案”早就曝光?|GBA编译
美国对伊“终极方案”早就曝光?|GBA编译 对话郑永年:斩首哈梅内伊后,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
对话郑永年:斩首哈梅内伊后,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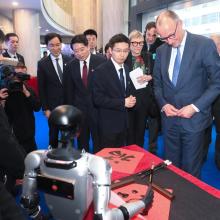 图解|与中国“脱钩”是错误!解析默茨访华背后的“双轨战略”
图解|与中国“脱钩”是错误!解析默茨访华背后的“双轨战略” “十五五”开局,靠什么实现增长?|独思录 x 郑永年
“十五五”开局,靠什么实现增长?|独思录 x 郑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