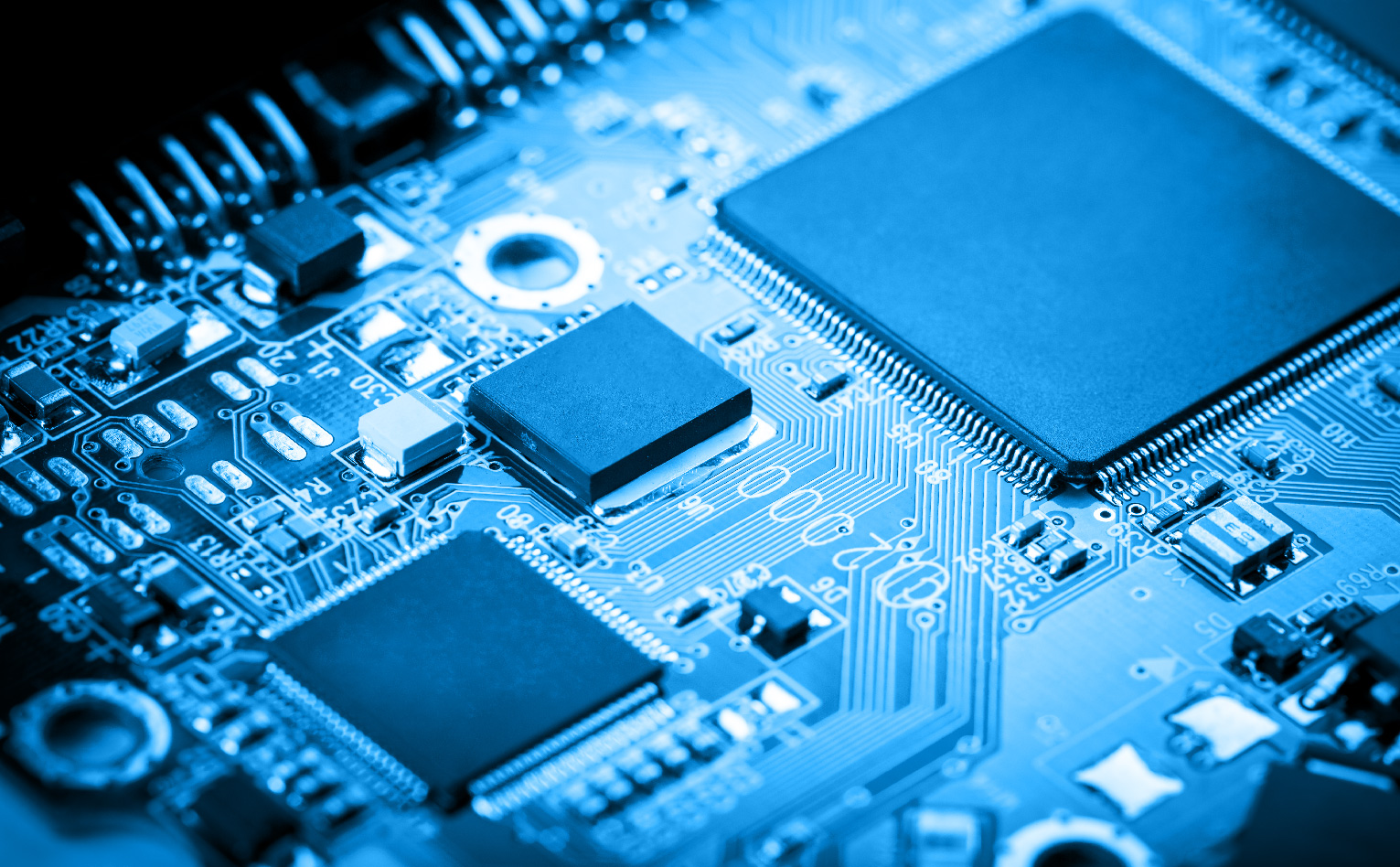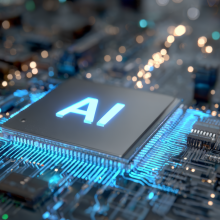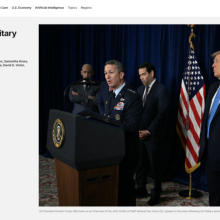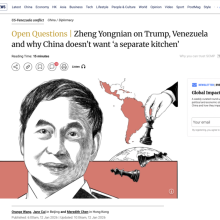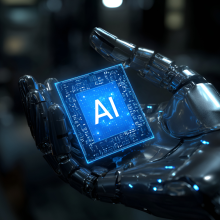编者按: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经济乃至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前沿。本文作者以全球半导体地缘竞争为宏观背景,系统梳理“芯片战争”下美欧产业政策之局限,以行业巨头为例,实证剖析技术迁移的艰难。本文指出,基于这样的背景——全球格局的重大转变的时刻,对中国与东盟市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和东盟需要加强区域资产和机构建设,以便更好地利用和抓住全球价值链变化带来的机遇,推进区域共同市场建设,从而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争取更多发展机会。东盟需以区域协同为钥,方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与中国共探合作新章。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我更为熟悉的半导体产业,以及在所谓“芯片战争”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前景。我非常高兴今天这里有来自深圳半导体协会和马来西亚半导体协会的两位行业协会执行成员,希望我们今天能就此展开更多交流。
一、全球半导体产能转移的艰难真相
大家都非常清楚,半导体产业已经成为中美之间经济乃至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前沿,以至于我们用“芯片战争”这个词来形容前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举措。美国曾出台巨额激励措施,试图将半导体生产带回本土,欧洲也在试图吸引半导体产业回流至欧洲。实际上,这类产业政策在世界多个地方都有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我认为,针对美欧“芯片战争”的这类产业政策,本质上带有被动防御性质。至于这类政策是否能真正有效地实现半导体生产回流,还未可知。
接下来,我会进一步论述美国的“芯片制造振兴计划”并不一定能拯救我们熟悉的英特尔;另外中国投入的3500亿美元支持也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推动技术前沿发展方面。一年前,拜登总统访问英特尔时宣布给予80亿美元补贴以促使生产回归美国,但这笔资金能否落实,仍有不确定性。穿插一则行业背景——全球三大半导体巨头,即台湾的台积电、韩国的三星和美国的英特尔,每家每年都轻松投入20到40亿美元在各自的工厂建设上;也就是说,这三家公司每年合计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在自行投入建厂方面资金非常雄厚。
以台积电为例,其现任董事长兼CEO魏哲家2022年12月在台湾南部宣布3纳米晶圆厂投产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想建自己的晶圆厂,但这现实吗?如果这么容易,世界上早就到处都是晶圆制造厂了。事实上,台积电公司内部将技术从新竹转移到台南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把技术和生产线搬到美国了”——因为半导体制造不仅仅是精密机器和工厂,关键是那几百位真正懂得如何“用厨房”做出最佳“汉堡”的工程师。尽管近期台积电宣布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的计划,为美国制造业再添动力,特朗普也十分高兴,但这个举动值得仔细分析。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是在2020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达成的协议,但直到最近才开始量产4纳米工艺。从建厂到量产要花4到5年,不是那么简单。如果真像想象的那么容易,早就实现了。另外,台积电曾承诺3纳米晶圆厂会在2025年准备好,但实质上是从2022年12月就开始建设的,这意味着美国大概需要5到6年时间从4纳米做到3纳米的晶圆片,而且2纳米晶圆厂甚至会更晚才能完成,毕竟台湾的2纳米厂今年下半年才刚开始投产。总之,建厂的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然,延迟还源于各种原因,比如劳动力限制、监管障碍、复杂的合规要求,尤其是在亚利桑那州的本地芯片制造体系里——即便英特尔在那里已经存在很久,但需求不确定,导致其位于俄亥俄州的晶圆厂原计划今年启动生产,现在也推迟到2030年才能完成。不难看出,转移芯片生产线这件事实际上有多么困难。
二、中国与东盟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那么,这对中国和东盟市场有什么启示呢?从数据上看,2023年半导体表现不佳。虽然2024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只是在一些细分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领域。即使是存储芯片,表现也不算好,其他类别的芯片,尤其是电脑用芯片,也不太理想。同时,了解主要的半导体市场非常重要。举例来说,服务器市场去年表现不错,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需求推动。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市场虽然重要,但市场需求并不强劲。再看市场预测,2024年半导体市场预计会有增长,2025年可能会恢复,但鉴于当前的种种情况,我们预计今年的复苏不会太明显。
现在,哪些市场对半导体最重要呢?首先看通讯领域,如果按数量计算,在大约5000亿美元的市场里,1700亿美元属于通讯领域,主要是智能手机;其次是笔记本电脑,占约1400亿美元;然后是汽车及其他领域。换句话说,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非常重要,约占所有芯片产量的35%到40%。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要考虑谁是这些产品的主要购买者,这后面会有重要影响。具体比例上,大约32%用于智能手机设备,25%用于电脑。这些产品就是你我日常使用的产品。
从新加坡的角度看,我们确实参与半导体价值链的前端,其他邻近国家参与的是所谓的后端工序——也就是从晶圆中提取芯片,封装到设备上,再做键合,叫做组装和封装,然后进行测试。组装、封装和测试服务遍布很多东盟国家。不过就市场份额和角色而言,东盟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份额仍然比较有限。全球市场主要由美国主导。虽然美国生产的芯片不多,但它是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比如,台积电25%的业务是为苹果生产芯片,也就是说苹果掌控了其产能的四分之一。因此,许多亚洲国家并非主要控制全球市场,而是成为主要的生产基地。
那么,东南亚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很清楚,东南亚借助美欧芯片法案等政策变化,抓住部分生产活动的转移机遇,这也改变了产业格局。与此同时,东亚整体是芯片需求的重要市场,特别是在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领域。我的研究发现,自2015年以来,亚洲整体市场在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需求上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换句话说,市场需求正逐渐向东亚转移。
东南亚有哪些国家级的举措呢?越南正在积极推动其半导体产业,主要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来发展芯片的前端制造。菲律宾则非常关注扩大组装、封装和测试服务,也就是所谓的后端服务,这些环节相对更依赖劳动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既有前端晶圆厂(即制造晶圆的工厂,从晶圆中提取芯片),也有后端服务。更重要的是,两国在芯片设计服务方面表现突出,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高附加值活动。就马来西亚而言,目前大约生产全球7%的晶圆,约占东盟地区组装、封装和测试服务的13%。在后端服务方面,亦是东盟最大的国家;其前端制造上略逊于新加坡,后者的份额约为10%。具体到马来西亚有英飞凌(Infineon)的前端晶圆厂以及强大的后端服务,英飞凌和英特尔也都有新的投资计划,希望能顺利推进。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不太受美国待见,而菲律宾虽然目前只占后端服务约5%的份额,但由于与美国关系较好,受益于所谓的芯片法案,份额存在大幅提升的可能。新加坡目前生产全球约10%到11%的晶圆。尽管新加坡是个小红点国家,但它制造了全球10%的芯片,虽然不是最先进的那部分,但新加坡生产了大量的半导体设备,约占全球设备制造的五分之一。新加坡有很多前端晶圆厂,近期也承诺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但这些晶圆厂并非最先进的类型。由于建设最先进的3纳米晶圆厂需要约300亿美元,因此新加坡目前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较低端的制造能力上。
泰国也有提升组装、封装和测试服务的雄心。富士康宣布将设立新的设备制造厂,英飞凌将在泰国建新的后端晶圆厂,目标是到2029年投资150亿美元。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泰国在美国眼中没有特别的问题。另外,越南目前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份额只有大约1%,计划通过其国家半导体战略和国家主导的投资,以及像Amkor这样技术上属于美国公司、但总部位于韩国的企业计划加强其在组装、封装和测试服务方面的布局,争取占据全球市场8%到9%的份额。
从历史地看,日本曾在上世纪80年代领先全球半导体行业,占据全球市场50%。然而,正如大家所知,今天的日本已不复当年之勇,主要是由于美国对日本实施了第一轮301条款的制裁,导致日本生产网络向东南亚大规模扩散。而当前,我们同样面临一个全新的环境,是全球格局的重大转变。对于东盟来说,我们需要加强区域资产和机构建设,更好地利用和抓住全球价值链变化带来的机遇。根据已有的经验,东盟应考虑如何利用其他地区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内部日益增长的需求,推进区域共同市场建设,从而在半导体产业等领域争取更多发展机会。
最后,如果各位有兴趣继续了解半导体相关话题,可以阅读我2022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深入了解全球电子产业;以及我作为主笔之一撰写的《2023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中关于半导体产业的章节。谢谢大家。
*本文系作者在由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合办的“第三届中国-东盟经济关系研讨会:高水平开放与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上的发言整理。
GBA Review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