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是指别国、特别是西方学界(政策界)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的专家学者,也被称为“汉学家”“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如今,在美国对华战略中,“中国通”将在具体对华战略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研究其共同特征和变化,对于研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编者按 · 2024.3.14
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是指别国、特别是西方学界(政策界)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的专家学者,也被称为“汉学家”“海外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所从事的研究,我们称之为海外中国学、海外汉学等,涉及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由于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基础性关系,美国的“中国通”更为受到中国的关注。这些“中国通”在学术和政策上的影响力大,多数曾在美国决策体系中任职,他们的对华观点往往能够影响本国对华决策以及对他国民众对中国情况的感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也受到中国决策层到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的关注。
如今,在美国对华战略中,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的总体判断已经定调。可以预见,“中国通”将在具体对华战略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研究其共同特征和变化,对于研判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政治和外交领域,分析美国的“中国通”所发生的变化。
从美国的“中国通”说起
2015年1月,中国的外交学院召开了“美国知华派与未来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根据“对美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三大指标测算,包括了大卫·兰普顿、沈大伟、金骏远、李成和李侃如等著名对华研究学者,这些学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美国对华研究的领军人物,具有相当代表性。

美国知华派排名(图源:外交学院“美国知华派专家评估项目组”报告)
(一)从美国“中国通”的学科分布看
美国大学的政治学一般为5-7个细分方向,包括:1)政治哲学;2)美国政治;3)比较政治;4)国际关系;5)政治经济学(有时与经济学系共享);6)战略与安全研究;7)方法论。
“中国通”学者普遍归属在比较政治、战略与安全研究以及国际关系三个方向,彼此之间存在交叉重叠。“中国通”在美国构成了东亚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彼此之间具有学脉谱系的传承关系,从费正清、鲍大可到黎安友、兰普顿、沈大伟、李侃如、谢淑丽、白邦瑞,再到新一代的傅泰林、蔡斯、毛雪峰、白洁曦、吴志远、迈克尔·贝克利、江泰乐等。美国的“中国通”总体上形成了接续有序的人才梯队生态,能够持续输出对华观点和研究成果,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战略思想力量。

大卫·兰普顿在“2023年香港中美关系论坛”的特别对话活动中接受了《中美聚焦》驻美编辑马克(Marc)的采访(图源:China-US Focus)
(二)从机构分布看
遍布高校和智库,并且呈现从高校转移到智库的趋势
高校机构和社会智库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决策中发挥了多重积极功效,特别是在对华政策方面,发挥了以下作用:
1. 美国对华重大战略思想和新兴概念的创新源头;
2. 美国中国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场所;
3. 多元战略思想交锋争论的辩论场;
4. 为军政退休退役、政党轮替涵养战略思想人才的“蓄水池”;
5. 美国讲“中国故事”(更多是中国“威胁论”“崩溃论”“衰退论”)的战略舆论力量;
6. 世界各种势力前往美国华盛顿表达对中国态度的载体平台,往往推动了中国内外部问题的国际化、复杂化、污名化(如南海、人权、边境冲突等)。
1.高校中既包括政治及国际事务学院,也包括挂靠高校设立的智库
比较著名的国际事务和政治学院包括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问题研究院、普林斯顿大学伍德威尔逊国际事务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乔治城大学沃尔什外交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等。有实力的高校也会聚焦国际关系和战略安全成立高校智库,比较有名的有哈佛大学的贝尔弗国际事务研究院、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事务研究院(与政治系的安全项目有重叠)、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乔治城大学新兴技术与国家安全研究所等高校智库。
2.社会化智库的战略作用更加突出
美国的社会化智库体系高度发达,一般以非营利独立法人的形式存在,既相互充分竞争,又有所分工专长,在对华决策中具有重要份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情局等)对华开展外交攻势的高端人才储备基地。比较代表的有兰德公司、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CSIS),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研究所、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2049研究所、哈德逊研究所、传统基金会以及卡特研究所等。这些智库的资金来源,既有政府委托项目,也有社会捐赠,也包括自身项目盈利,总体上实现了良性的“自我造血式”发展。
美国“中国通”的共同特征
成为美国的“中国通”,一般应当具有三个重大特征:
(一)首先是中国问题专家
从中国具体领域问题研究进而成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其对中美关系的研究具有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证基础。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证基础,更加注重事实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结论观点,较多使用田野调查、案例研究、开源信息分析以及后来兴起的定量工具。
也就是说,美国“中国通”的中美关系研究是往往建立在对中国问题的坚实基础之上,从中国问题到中美关系的递进发展次序。 美国的“中国通”往往在硕、博士阶段就开始掌握汉语,并选定中国某个特定领域的问题进行研究,如军事安全、军事科技、对外冲突、外交行为、经济政策、精英政治、抗争政治等领域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成为了中国特定领域的专家,建构个人初期的学术声誉。伴随着学术积累和学术职位的稳定,逐渐参与对华公共政策的讨论、决策顾问咨询。一部分高校教授和智库学者,会通过公开发表评论、学术文章和专著来系统性地阐述其思想,也有一部分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从学入仕,担任国防部、国务院等负责中国和东亚事务的官员,或是成为高级政治领导的咨询幕僚,从而将学术上的思想和理念付诸于实践。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图源:AP)
(二)具有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影响力
其提出的战略思想或是理念,能够影响甚至主导美国一段时期或是某一些高级领导人的对华政策,从而为中美的决策层所关注。
没有政策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学者很难称之为“中国通”,如哈佛大学政治定量方向的Gary King教授,近年运用中国公开数据发表了多篇政治学顶刊《美国政治学评论》,是该刊物发表关于中国话题的数量之最,但是无论是其本人或是外界,都未曾将其称之为“中国通”。
因此,要成为美国的“中国通”:一是与政策问题保持着密切距离,从自身研究特长出发,持续关注中国发展态势和双边关系,及时进行战略研判、观点输出、公开发声、咨政建言等活动。二是与政策决策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距离,如通过“旋转门”机制(学者与国家安全体系的人员交流)出任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众议院委员会职位,或是成为政治领导或机构的咨询顾问,参加国会听证会进行作证,围绕中国发展和双边关系写作报告、答疑质询。如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美国政府于2000年10月通过国会授权设立,主要负责监督和调查中美之间的国家安全和贸易问题。成员由两党国会议员所任命,每年发布年度报告,被认为是美国白宫、国会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指南),其报告的撰写成员多数来自美国国内高校和智库的顶尖中国问题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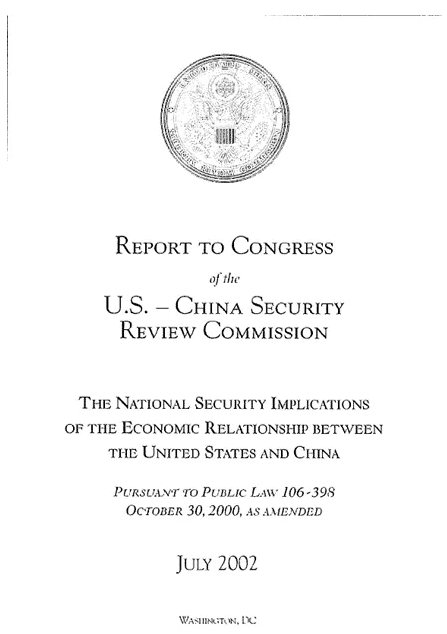
《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2022年度报告》,该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首份年度报告(图源: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官方网站)
(三)与中国各阶层保持着广泛的接触
与中国各阶层(至少是对美关系机构和研究机构、学者)保持着广泛的接触,能够较为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文化和态度。
老一代“接触派”的“中国通”往往在青年时期就通过到中国访问交流、学习汉语、旅行、田野调查等多种方式与中国建立了亲密的联系。甚至许多“中国通”与中国人结成了婚姻,如费正清、黎安友、Hal Brands,他们对中国有着较一般美国学者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亲近,对中国文化和人民抱着更为友好和客观的立场。他们也会通过招收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与中国政府人员的接触交流,与中国方面保持了较为直接和真实的接触,因此,他们能够以更为冷静客观的视角观察中国的世纪发展情况。

费正清(1907-1997)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图为在北京四合院举行婚礼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图源:央视网)
美国“中国通”群体的一些变化
1.美国的“中国通”群体面临遏制派崛起、接触派压制的结构性压力
近些年,在中美战略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对华相对客观友好的接触派“中国通”(如兰普顿)被压制,主张对华强硬的“遏制派”学者崛起,并逐渐主导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权,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形成了“思想—政策共振”,许多不理智、不客观、对抗性的话语进入了双边的对话论战。(在相关研究中可见,David M. McCourt(2022)发表在《安全研究》上的“Knowledge Communities in U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American China Field and the End of Engagement with the PRC”《美国中国学研究与接触派的终结》)
2.美国新一代在高校生存的“中国研究”学者,不自觉地与现实的中国拉开了距离
为了能够在高校的终身教职考核中通过,也不得不更加倾向于采用定量研究,利用更短时间“冲刺”顶刊,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在数据中造论文”“在黑板上研究中国”的问题,造成了这些学者很难(甚至无意于)深刻理解中国的现实政策问题,也难以了解政策和问题背后的隐性信息。这既受限于激烈的晋升考核压力、美国政治学科的整体定量转向影响,也因为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学者在中国访谈调研的难度加大的原因。
我们可以初步观察到,美国对华研究逐步出现了高校“学院派”和智库“政策派”的分野,并且智库“政策派”的学者更为积极的现象。这一学术与政策的分离,间接上也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缺少了历史穿透力和理论说服力,往往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感、短视感、局限感,缺少了宏大的整体性视角。
3.“中国通”专家学者逐渐往中国的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领域集中
相比于老一代“中国通”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话题的关注,新一代“中国通”似乎更加青睐军事安全,他们选题时往往更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军事科技、战略威慑等传统战略与安全领域,逐渐成为美国新一代“中国研究”的显学领域。笔者所接触的一些在读美国博士,发现他们更加倾向于研究中国的军事与安全话题。这一转向,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高度关注中国的军事发展、话题热度高、国防部和各界的“慷慨”资助,适用范围广,不少博士也具有军事背景;另一方面,笔者猜测,也是因为该领域数据可得性差(有人诙谐地称之为“政治学定量霸权的一块净土”),更强调基于开源信息的分析,对定量和一手调研访谈的要求相对低一些,更适宜政策导向的研究。
新一代“中国通”不约而同地向军事战略与安全领域的转向聚焦,既凸显了今后中美两国关系中对抗性因素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主导今后一段长周期的新“中国通”们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客观甚至“疏离”。他们是将中国当作一个冷静客观分析的对象国,而非是试图理解其历史和文化内涵、注入个人情感和学术理想的田野国家。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中国通”已不再“通”,他们更加专注于中国的某个具体问题。例如,目前已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迈克尔·蔡斯(Michael S. Chase先后经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兰德公司、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高级问题研究院),其专长在于研究中国海上安全及军事现代化,对中国军队的改革、海上军事力量等问题具有较好的研究积累,但是很难看出其对中国其它领域的关注和兴趣。相比于其导师兰普顿教授对中国的整体性理解和换位思考,查斯对中国的态度更加专注、客观、疏离。因此,主导未来中美关系战略思想创造的“中国通”们向军事安全领域的转向趋势,将会间接影响今后中美两国关系的宏观视角和微观操作的态度。

迈克尔·蔡斯于 2021 年 5 月在美国防务学院的校园访问(图源:DVIDS)
美国的“中国通”真的“通中国”吗?
美国的“中国通”群体是中国开展对美关系,甚至是审视自身战略决策所不可忽视的战略思想群体,他们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给中国“照镜子”“扯袖子”的外部“吹哨者”作用。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开展对美“二轨外交”的重要桥梁和渠道,特别是在中美关系面临困难和危机处置时期,当官方通信渠道受阻,或许中美双方的专家学者将发挥灵活柔性的连接作用,有利于给中美关系装上“减震器”。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战略界对“中国通”群体更是有所批评,认为他们没有预测中国对美国日益严峻的战略挑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在彭博社发表专栏,把观察中国的专家分为“中国通”和战略学者两类。他认为在冷战后认识并且宏观把握来自中国的挑战方面,大国战略专家往往对中国的未来意图预测得更准确,许多最具前瞻性的文章都不是出自“中国通”之手。面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中国通”和知华派往往都没有作出正确的预测,而是那些没有专门钻研中国的大战略专家准确预测到了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挑战。
大国战略专家大部分不是“中国通”,他们通常不通汉语,也没有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他们更多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全球竞争对手”而非一个历史悠久的独特文明。相比之下,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文化、掌握和中国政治阶层的联系渠道且有许多中国社会关系的“中国通”,更为精确地把握中国的政治、历史和战略,却无法预测中国的未来。 针对这样的批评,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对美国的“中国通”所提出的更高要求,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美国的“中国通”在影响美国战略决策、加强中美双边交流理解、避免战略误判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们或扎根高校著述育人、或游走智库“兜售”思想、出仕入学、庙堂民间,成就了美国一道独特的知识份子群像。 如果更进一步地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多方面原因,美国的“中国通”或许也很难“通中国”了:
1. 海外中国学研究进入更加细分的专业化分工
海外中国学研究会进入更加细分的专业化分工,“中国通”更准确地说是“通晓中国某个具体领域”,如军事安全、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等。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建构已经较成规模,为了应对日益激烈化的研究竞争,专注细分领域成为海外中国学发展的必然阶段,老一代基于宏观视野总体把握的“中国通”已经逐渐被具体领域的中国问题专家所接替,“中国通”已很难“通中国”。
2. 学院派学术研究和智库派政策研究的分野将继续拉大
学院派学术研究和智库派政策研究的分野仍将继续拉大。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初步趋势:美国从高校学者身份进入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任职的现象日益减少,转而由大量在智库工作的政策分析专家进入“旋转门”。也鲜有退休官员进入高校担任教职,且往往担任高校智库的高级研究人员,而非重回学术道路。美国战略与安全领域的学术与政策在冷战后期已发生较大分野,以致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一代战略大师从学术界的退出,这一学术与政策的隔阂趋势仍将在海外中国学中继续发生。
3. 海外中国学逐渐转向更为抽象的学术理论建构
随着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日益成熟,海外中国学要成之为学,也必然会摆脱接近于情报分析或新闻报导式的描述性分析,转而走向更加具有高度抽象特征的理论建构。海外中国学已经不再局限为区域和国别研究,既强调对政治学主流理论和比较政治的最新成果的应用,同时也强调对主流政治理论的贡献。
结 语
美国的“中国通”和中国的“美国通”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体温计、连接桥、减震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我们也应当积极欢迎新一代美国学子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到中国亲自感受、与中国人交朋友,或许这更能奠定中美未来关系的整体走向。与之相对应,中国新一代学人也应当继承和发扬老一代学人的学术传统,成为新一代中国的“美国通”。后续文章将围绕“中国如何产生‘美国通’”继续分析为什么当前我们还很难培育起与美国“中国通”相比肩的“美国通”。
本文作者
梅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
*原创声明:本文版权归微信订阅号“大湾区评论”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侵权必究。公众号授权事宜请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权事宜请联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Review 新传媒
评论文章
 今日伊朗,明日古巴?特朗普的“第三目标”|GBA编译
今日伊朗,明日古巴?特朗普的“第三目标”|GBA编译 袁太平、朱静慧:巴阿边境冲突对出海央企国际经营战略版图拓展的影响分析与建议
袁太平、朱静慧:巴阿边境冲突对出海央企国际经营战略版图拓展的影响分析与建议 评兰德公司报告: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竞争本质是“社会竞争力” | 科技观察
评兰德公司报告: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竞争本质是“社会竞争力” | 科技观察 周承哲:凯文·沃什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逻辑的“体制性调整”|全球改革观察
周承哲:凯文·沃什对美联储货币政策逻辑的“体制性调整”|全球改革观察 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引发跨区域反击行动 | 全球地缘政经动态(2026年第4期)
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引发跨区域反击行动 | 全球地缘政经动态(2026年第4期) 对话郑永年:美国2小时斩首哈梅内伊,中国还要让AI只做“烟花”吗?
对话郑永年:美国2小时斩首哈梅内伊,中国还要让AI只做“烟花”吗? 美国对伊“终极方案”早就曝光?|GBA编译
美国对伊“终极方案”早就曝光?|GBA编译 对话郑永年:斩首哈梅内伊后,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
对话郑永年:斩首哈梅内伊后,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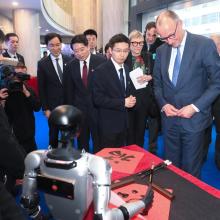 图解|与中国“脱钩”是错误!解析默茨访华背后的“双轨战略”
图解|与中国“脱钩”是错误!解析默茨访华背后的“双轨战略” “十五五”开局,靠什么实现增长?|独思录 x 郑永年
“十五五”开局,靠什么实现增长?|独思录 x 郑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