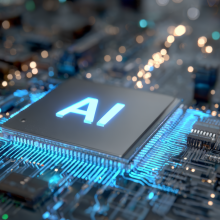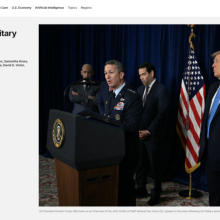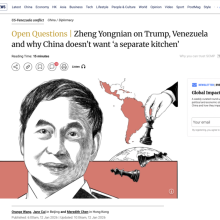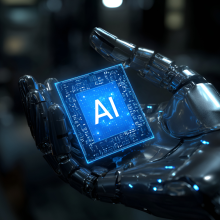编者按:美国国内正经历着“特朗普之变”。从政党政治,到三权分立制衡体系,再到中央地方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内部秩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构,也正在深刻影响着外部的民主秩序、区域秩序与国际秩序。
有人已经把“特朗普之变”比喻成为美国的“戈尔巴乔夫之变”。本文指出,“特朗普之变”并非特朗普个人引起的现象,而是美国结构性矛盾的爆发,并在逐渐重构美国内部内部秩序、外交政策,并对全球传统“自由国际秩序”造成冲击。这场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初心的变革,最终会演变成一场可控的宪政改革,还是导致美国秩序解体的“戈巴乔夫之变”,仍有待观察。
一、前言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大国之变。一个大国之变所能释放出来的能量并非任何一个较小国家之变所比拟的。近代之前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等,冷战时代的苏联,都可以视为是当时的大国。这些大国的解体至少彻底改变了四个秩序,一是国内秩序,二是与该大国关联的那些国家的内部秩序,三是该大国和关联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区域秩序,四是国际秩序。
今天要讨论的大国之变,即特朗普的美国之变。美国自建国以来践行宪政体制。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美国视为是宪政体制的典范,美国人自己对这个体制有着无限的信心,而其它国家则更是把美国视为是自由民主的灯塔,梦想自己的国家也可以拥有类似美国那样的体制。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美式民主被普遍视为是“历史的终结”,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以美国宪政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不仅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政体,也是最后的政体。人们也普遍地相信,美国的宪政体制“牢不可破”,有能力纠正几乎是所有的错误,消化任何权势人物因为个人因素而对体制所构成的影响,应对任何时代变化所构成的挑战。在外部,对美国的邻居和其它亲美国的国家来说,美国也是他们所能拥有的可以打交道的国家。美国被视为是拥有“正义感”,只要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在他们求助于美国的时候,美国总能出手相助;美国的外交行为被视为是“透明的”和“可预测的”,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影响美国对他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即使有些时候的美国政府不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他们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等待一位新的总统去纠正过去的错误。
如此,美国不仅构建了被视为是“最理想”的国内秩序,深刻影响着其它三个外在的秩序,尤其是二战以来。
第一个秩序即是世界上各国的民主秩序。尽管美国不是西方民主的创始国,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民主在诸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西方其它国家来说,美国民主无疑是它们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对其它国家向往民主的人们来说,美国无疑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而美国本身也竭力向其它国家推行美式民主,甚至把美式民主强加给他国之上。
第二个秩序即是美国所构建的区域秩序,尤其是盟友体系。美国把那些亲美的力量用联盟这一制度形式统合起来,构成了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
第三个即是国际秩序。美国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在国际秩序建构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再加上美国的联盟体系,促使美国更加有能力维持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其实,对美国来说,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就是整个国际秩序的核心。
二、“特朗普之变”:美国内部秩序的重构
但现在则很不一样了。美国国内正经历着“特朗普之变”。有人已经把“特朗普之变”比喻成为美国的“戈尔巴乔夫之变”。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之变”导致了四个秩序的变化:一是苏联的解体,即内部秩序的变化;二是东欧国家内部体制的变化;三是苏联为核心的华约体制的解体;四是国际层面地缘政治秩序的变化。而一些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开始担忧,美国内部的巨变是否也会直接导致其他三个秩序的巨变?
那么,首要的问题是,美国所经历着的“特朗普之变”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变化呢?毫无疑问,美国内部的变化是全方位的和史无前例的。人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1. 政党政治的变化
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也是美国式民主的基石。建国以来,尽管美国的政党制度也经历了诸多变化,但始终没有任何结构性的变化。但今天,美国的政党制度已经被高度“特朗普化”。特朗普先是把共和党改造成为“特朗普共和党”。通过民粹主义的方法,特朗普把传统的共和党人排挤出共和党。这种变化也影响着民主党的政治方法。面临共和党的民粹主义压力,民主党也不得不诉诸于民主党特色的民粹主义。尽管美国依然是共和民主两党,但这两党已经不存在任何共识,所具有的仅仅是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今天美国两党政治趋势不能被扭转,那么党争必然是美国社会内部冲突的制度基础。
2. 三权分立制衡体系的变化
美国宪政的核心是三权分立制衡,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但特朗普似乎以其超人的能力破坏着这一体系。立法部门或者因为党争而处于瘫痪状态,或者因为特朗普所施展的“技巧”而把特朗普的意志强加给立法部门。特朗普对司法的干预更令人担忧。自其执政以来,司法部门成为了特朗普要整治的“深层国家”的核心部门,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各种政治和行政的方法使得司法部门就范。尽管司法部门(尤其是倾向于维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法官)不时地挑战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些内政外交政策,但特朗普总是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化解之。如果用传统的观念来看今天的美国,美国的三权分立制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说已经面目全非了。
3. 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
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而言,美国是双主权国家,即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官员都是由选民选出,并且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权限由宪法规定,并且是有限的。但是,特朗普正在快速改变这一局面。很显然,特朗普倾向于“亲”共和党执政的州和“反”民主党执政的州。他甚至不惜动用军队的力量对民主党执政的州和城市进行政治干预。
4. 意识形态的变化
在意识形态层面,特朗普代表的是传统并且是宗教味浓厚的共和党价值观。他竭力敌视和反对民主党的多元主义(DEI,多元、平等和包容)价值观、觉醒文化、LGBTQ文化等等。
应当强调的是,尽管特朗普在主导着这些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仅仅是特朗普本人的意志所为,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的。正因为如此,所有这些变化并非乌托邦,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人们可以把特朗普视为是变化的“中介”,也就是说,没有特朗普也会有其他人来主导这些变化。因此,人们所不能确定的是这些变化会通过何种方式发生及其发生到何种程度。
三、军事重点:“向内转”
这涉及到特朗普的行动方式及其这些方法的有效性。特朗普的行动方式五花八门,涉足各个领域,并且是互为关联。特朗普的行动方式毫无规则可循,往往给人莫大的惊讶,这也是美国和其它关联国家所担忧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可以举近来发生的军队将领神秘“峰会”为例。这个例子不是特例,但全面传达出有关“特朗普之变”及其方式的诸多重要信息。
9月5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国防部”改为“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成为其上任以来签署的第200项行政命令。9月30日,被美国防长紧急召回的全球近千名美军高级别将领,在华盛顿特区周边举行了一场被美国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神秘“峰会”。防长赫格塞思在会上宣布,美军必须做出重大改革。美媒称此次会议“罕见且高度政治化”,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则认为,美国政府此举意在为一场“内部战争”铺路。
赫格塞思在会上宣布,美军必须做出重大改革,全面清除削弱“战争部”杀伤力的“多元化政策”(DEI)。赫格塞思所宣布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对现役美国军人开展每年两次测试考核;现役军人在每个出勤日必须进行体能训练;减少线上课程,增加实战和射击训练;改革晋升制度,根据绩效和能力提拔优秀人才;取消“零缺陷”文化,让军官在维持纪律和标准时不受投诉或政治压力影响;剪短发、刮胡子,严格要求外表仪容等。
如果赫格塞思的行为是人们预期中的,并且也可以认为这些改革也合乎情理,那么特朗普的出现不仅出乎意料,而且其言论令人惊讶。特朗普起初似乎对此次集会并不知情,他曾表示:“如果他们邀请我,我会去”。而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两天,特朗普决定出席这场美军高级将领集会。
美国的媒体普遍认为,如果说赫格塞思主持这场会议是为了宣布改革新规,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这场会议就好比一次“忠诚度测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似乎看得更深一层次,认为,在特朗普看来,“忠诚”之所以在眼下尤其重要,是因为他即将要开启一场“内部战争”。在集会的演讲中,特朗普说,我们应该把一些危险城市,当作军队、国民警卫队的训练场······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洛杉矶这些地方非常不安全,我们将一个一个清理整顿。这对今天在场的一些人将是重要任务。这也是一场战争、一场来自内部的战争”。
美国新闻网站AXIOS直言,特朗普向将军们传递出的信息简单明了:要么做好准备在一支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化的军队中迎接一场内部战争,要么起身走人。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场神秘“峰会”是“美军的转折点”。《华盛顿邮报》则报道,在这场神秘军事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五角大楼已将《国家防务战略》(NDS)和《全球部署审查》(GPR)草案分发至华盛顿美军总部以及全球各地的联合司令部。分析普遍认为,草案的分发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将国防政策的重点转向国内防御和西半球。
这里的关键词是“国内防御”与“西半球”。
就“国内防御”而言,根据MAGA目标治理内政一直是特朗普的头等要务。这次神秘峰会召开几天之后,10月4日,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州长普里茨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今早,特朗普政府的‘战争部’向我发出最后通牒:召集你们的部队,否则我们就来做。”美国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当天证实,特朗普决定向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部署国民警卫队。不过,芝加哥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芝加哥是继华盛顿、洛杉矶、曼菲斯、波特兰后,又一个被锁定部署部队的民主党执政城市 。
随着特朗普将军事重点“向内转”,多个美国城市正在推行“华盛顿特区模式”,就是说,联邦执法部门与地方警察局联合行动常态化,国民警卫队听命于总统调遣,以打击犯罪为名,实现军权“联邦化”。
10月6日,特朗普甚至扬言,要动用“暴乱法”(Insurrection Act)在民主党主导的美国城市部署更多的军队。历史上,美国总统根据“暴乱法”可以在美国境内部署军队、并在特定情况下将各州的国民兵(National Guard)联邦化,例如镇压内乱、叛乱、以及反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武装叛乱。理论上,总统只能在超出民政当局处理能力的危机下动用暴乱法,但这项法令并未充分定义总统可以在何时、何地部署军队。总统可根据暴乱法,在不同情况下进行军队部署。美国历史上暴乱法被援引了数十次,但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暴乱法就鲜少被引用。暴乱法最近一次被援引是在1992年,时任加州州长向老布什总统(George H.W. Bush)请求军事援助,以回应因为4名洛杉矶警员殴打非裔驾驶金恩(Rodney King)被判无罪后引发的致命暴动。而自从约翰逊总统(Lyndon Johnson)以来,就不曾有美国总统无视州意愿单方面援引暴乱法。约翰逊在1965年未经州长同意动用国民兵,以保护阿拉巴马州的民权示威者。
从名义上说,特朗普在这些城市的作为是针对犯罪和非法移民的。这是MAGA运动目标的一部分。正如白宫女发言人杰克逊透过声明指出的,“特朗普总统不会对困扰美国城市的无法无天视而不见”。除了在这些城市大规模扫荡犯罪与非法移民外,美最高法院也出面挺特朗普, 撤消了30万委内瑞拉移民的临时保护,支持特朗普推动大规模驱逐移民出境政策的核心目标。
也不难发现,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以种族政策为核心的。特朗普一方面拟设难民上限7500人,为历史新低,另一方面则把具有欧洲血统的南非白人(Afrikaner)为优先收容对象。
四、外交重点:从“周边”到“后院”
特朗普的“转向西半球”政策则以更深刻的方式影响着更多的国家。今天,特朗普的政策的优先次序是:国内-周边-后院。
美国的周边比较简单,只有两个国家,即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是传统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美国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影响这两个国家。特朗普针对这两个国家的周边外交的政策目标似乎也很清楚,一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二是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的进入,三是更有效地控制和影响他们的政策。
拉美区域被美国视为是自己的后院。但对这个后院,美国的政策很难说是成功的。尽管门罗主义之后,这个区域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经济和政治结构上也高度依赖美国,形成了拉美学者所说的依附型发展模式,但拉美发展到今年依然是一个问题最多的区域,一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些国家依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并且各国都呈现为一个高度分化和分裂的社会,极左极右轮流执政,亲美和反美势力高度对立。拉美社会的社会治理能力低下,往往被美国视为是犯罪和毒品的来源国。
特朗普似乎要改变这种现象。特朗普已经宣布“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重新确立对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权,重新拉拢拉美国家来对抗所谓的“中国影响力”。如果拉拢不成,那么美国就会实行赤裸裸的暴力政策。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关系便是典型。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与委内瑞拉处于战争的边缘状态。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列举了种种迹象,认为美国与委内瑞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升高。如果两国之间有一天爆发了战争,那么没有人会感到惊讶的。
五、今天美国问题的本质刚好和苏联问题相反
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之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促成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那么,今天美国的“特朗普之变”是否会演变成“戈尔巴乔夫之变”呢?就内部来说,“特朗普之变”早就引出了美国内部就“美国是否会发生革命”的讨论。这一讨论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十足的理由的。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已经积累起诸多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要不通过激进的改革才能得到解决,要不通过更为激进的革命才能得到解决。特朗普把自己所做的称为“特朗普革命”。这场革命是以可控方式的进行下去,还是会演变成真正的革命,或者是半途而废?尽管这还需要观察,但这场革命,无论是可控的还是失控的,必须是深刻的,否则解决不了美国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不管美国内部的变化是怎样的,美国的“国内-周边-后院”政策次序的确立所影响的绝对不仅仅是这些内部变化,而是会深刻影响到前面提到的三个外在秩序。
1. “民主阵营”国家的内部秩序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二战以后,美国在推行和扩展美式民主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无论是美国内部的民主问题,还是美国减少对其它国家民主政治的投入,都会深刻影响这些国家民主的发展进程,甚至是生死存亡问题。尽管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中所指出的,历史上民主有进有退,但今天民主的“退潮”势头之强是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无论对哪个区域或者哪个国家,特朗普对美式民主的输出已经不感兴趣。特朗普已经取消了专门从事输出民主的部门,即国际发展署。
实际上,正如美国人自己所意识到的,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本身也不感兴趣。在发达的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全球右派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正在对传统民主政体产生巨大的影响,无论是福利和移民政策还是外交和国防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对一些国家来说,正面的消息是美国不再会像从前那样进行颜色革命和输出美式民主;对另一些国家来说,负面的消息便是民主的倒退,尤其是那些民主本来就很脆弱的国家。
2. 美国退出一些区域之后,这些区域的国际秩序的变化
自从美国进入世界体系之后,一直以各种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和其它大国相比,美国的利益已经深度嵌入各个区域秩序,成为这些区域秩序的内在一部分。自其执政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致力于想退出这些区域,至少减少对这些区域秩序的投入。迄今为止,退出这一政策往往会导致两个主要后果。第一,美国很难退出。一旦退出,美国在这些区域的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美国一旦强行退出,那么这些区域会陷入混乱状态。欧洲、中东的局势就是这样。同样,如果美国从东盟退出,东盟也几乎会产生类似的后果。
不过,应当意识到,特朗普的退出政策不是其本人的判断失误,而是因为此前美国的过度扩张,早已经使得美国支撑这些区域秩序方面力不从心了。人们可以认为,即使特朗普不做,其它总统迟早也会这么做。这就表明,各个区域秩序混乱的出现是早晚的事情。美国连像欧洲那样的盟友都可以抛弃,更不用说是其它国家了。“被抛弃”也是此前那些和美国关系紧密的国家今天所最担忧的;相应地,“不被抛弃”也是这些国家对美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3. 国际层面地缘政治秩序的变化
在国际层面,“退群”不仅是特朗普的政策,更会是副总统万斯这一代“80后”美国领导层的政策。特朗普的“退群”政策(巴黎气候协议、联合国体系、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的后果已经显现,无需作更多的论述。这里想强调的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的“退群”正在加速各个区域的“封建化”。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区域已经呈现出“群雄崛起、群雄逐鹿”的局面,尽管从长远来看,有可能形成人们所期望的多极体系(详见《一个世界,几个体系?》一文),但国际秩序的封建化性质很容易导向区域甚至是全球层面的冲突,甚至战争。
不管怎么说,“特朗普之变”是深刻的。问题在于,“特朗普之变”是否会演变成美国的“戈尔巴乔夫之变”?尽管美国和往日的苏联在一些方面的确也有雷同之处,尤其是国际层面的过度扩张,但更需要看到两者之间的不同,否则人们就会犯错误的战略判断。
今天,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依然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之中。这种情况把今天的美国和往日的苏联区分开来。“戈尔巴乔夫之变”是为了解决当时苏联所面临的发展停滞局面,从而触动苏联的变化,其初心是苏联的复兴。但戈尔巴乔夫的激进变革方式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尽管特朗普是MAGA运动的产物,也就是要促成“美国的再次伟大”,但美国并没有当时苏联所面临的经济和技术停滞不前的局面。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苏联问题的核心是其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有效地阻碍了经济基础和技术的发展,所以戈尔巴乔夫要改革的便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今天美国问题的本质刚好和苏联问题相反,即美国问题的核心是其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跟不上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特朗普要改革的对象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特朗普针对的对象是上层建筑,而非经济基础。经验地看,在经济基础面,特朗普所做的是要强化传统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实际上,无论是特朗普本身所代表的利益,还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要求特朗普所代表的利益,无论怎样的“特朗普之变”都不会改变美国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特朗普需要改革和所能改革的也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那么,就此而言,特朗普所从事的这场革命是否会促成美国传统宪政体制的巨大变革?尽管一些美国人已经称特朗普为“法西斯主义”,但这种“法西斯主义”是手段还是目标呢?这里没有答案。
正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特朗普之变”的初心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其所使用的手段会把这场革命导向何处呢?这需要人们的密切观察。
GBA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