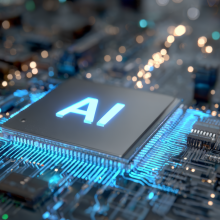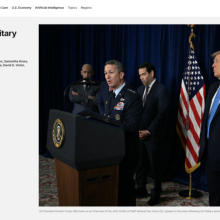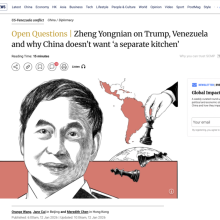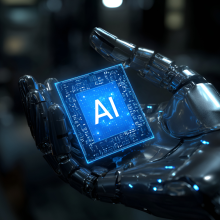编者按:以数量化模型AOCAI为核心工具,作者揭示了过去三十年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位移轨迹,突破了传统对“中立”与“对冲策略”的定性认知。通过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等多维指标,作者构建出一张动态演变的地缘政治热力图,呈现出一个愈加复杂、非线性且地缘重构中的东南亚图景。其最大价值,在于以实证数据动摇了“东南亚始终在中美之间维持等距平衡”的惯性叙事,指出:所谓“广结善缘”的外交理念,正在现实经济结构重塑下逐步退化为“选择性依赖”或“点菜式生存”。
本文强调经济依存度对战略倾向的深刻塑形,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占东盟贸易总量近四分之一。同时,中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增长迅猛,形成了以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发与新兴技术合作为支点的“经实安虚”复合依赖模式。这种模式在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表现尤为明显,其对华经济依赖已逐渐萎缩其对美安全合作的空间。而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中等国中,这种依赖虽然在表面上仍维持“对冲”姿态,但实质已在若干关键领域(如镍资源、电池供应链、数字技术)形成结构性倾斜。
然而,本文并未落入“经济决定战略”的线性逻辑,而是敏锐指出了东南亚国家在战略自主性上的反塑努力。无论是菲律宾通过加强与美军事合作交换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新加坡与日本共建“亚太数字信任框架”,亦或印尼主导“东盟电动车生态系统”、推动本地高附加值产业链建设,这些都表明:东南亚不是被动的地缘棋子,而是具有高度策略弹性的博弈主体。
东南亚国家正面临着三重矛盾困境:其一,战略安全层面,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虽声势浩大,却缺乏实质市场准入机制,无法与RCEP所代表的亚太自由贸易逻辑抗衡;其二,风险控制层面,中国对东南亚的投资虽带来增长机遇,却也引发主权与环境风险,例如缅甸密松水电站与老挝债务问题;其三,民意基础层面,东南亚民众对中国信任度始终偏低,与政府日益亲华的政策形成错位,或将在未来的国内政治中引发结构性反弹。
译者认同作者对东南亚战略倾向“缓慢但清晰地向中国靠拢”的判断,并认为文章提出的“选择性站队”与“无意识偏移”两大概念,对于理解当下区域战略行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经济重塑一切”的倾向,低估了东南亚国家在制度创新、技术治理与多边机制构建中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例如,近年来区域内出现的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去中心化合作”尝试,诸如印尼与韩国、日本在AI治理上的合作倡议,或马来西亚在区块链金融监管上的制度试点,已预示东南亚正尝试跳出传统安全-经济二元对立,向“新型战略资源主权”迈进。
未来十年,东南亚能否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回旋余地,将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在数字经济、绿色转型、制度创新等新兴领域构建不可替代性。这不仅是“夹缝中求生”的延续,更是“在裂缝中生长”的文明试炼。真正的中立,不是保持等距,而是构建自身不可或缺的价值与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东南亚的未来,不是中美谁赢谁输的附属变量,而是全球秩序重组中的关键变量——这或许才是本文最深刻的启示。

*本文原载于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原题为“Southeast Asia is Starting to Choose: Why the Region Is Leaning Toward China”,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一、东南亚7亿人口的选边困局?
相比于世界多数地区,东南亚地区日益深陷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漩涡之中。纵观亚洲地缘格局,主要国家已形成相对明确的阵营分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支持美国阵营;印度呈现出向美国靠拢的战略倾向,而巴基斯坦则与中国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中亚多国亦不断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协作。然而,在东南亚这个拥有近7亿人口的地带,仍有广阔的角逐空间。哪个超级大国能够成功争取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关键国家,使其政策路线与己方保持一致,就更有可能强化其在亚洲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战略优势。
然而,数十年来,东南亚各国领导人始终拒绝“选边站”。尽管中美竞争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核心议题,该地区政要仍在外交上秉持“广结善缘”的原则。当然,他们并非对地缘格局的嬗变毫无觉察。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2018年所言:“保持中立固然理想,但或许形势终将迫使东盟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希望这一时刻不会过早来临。”
李显龙对这一困境的研判,不仅代表了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立场,更折射出国际社会的普遍忧虑。以新加坡为例,这个在全球化时代蓬勃发展的国家,始终以门户开放的转运港(entrepôt)自居;表面奉行威权主义的越南,已成为贯通中西方供应链的重要制造业枢纽;曾经深陷内乱泥潭的印尼、菲律宾等群岛国家,自2000年以来GDP均实现显著增长。当东南亚国家官员拒绝“选边站”,实质是在表达对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坚持——这种秩序以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逐渐消弭的地缘博弈为特征的时代图景。
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这一秩序开始瓦解。如今,东南亚国家已深陷大国竞争的漩涡之中,中美在亚洲地区的对峙日益尖锐。而东南亚各国无论意愿如何,都已难以规避大国博弈带来的压力。当把东南亚十国的涉中美表态置于同一坐标系中观察,一个趋势已然明朗:过去三十年间,多数国家正经历着虽缓慢但清晰的战略位移——逐渐疏离美国而向中国靠拢。某些国家的转向尤为显著,尽管仍有少数国家成功实施“对冲”策略游走两强之间。但总体航向已不言自明:东南亚国家虽坚称自己保持中立,其政策取向却整体向中国靠拢,这一态势对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抱负带来了严峻挑战。
二、实力角逐:中美的东南亚影响力之争
根据洛伊研究所“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通过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影响力等多维指标衡量各国相对实力)的评估,到2010年代末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已达到美国的近九成。这一跃升既源于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更得益于其成功将经济成就转化为外交、军事乃至文化领域的战略优势。中国的崛起曾引发1990年代美国学界的激辩:究竟应该遏制还是接触这个崛起的“亚洲巨人”?接触派最终占据上风。尽管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任内中美关系时有波折,但始终未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9·11”事件后中东战事分散了美国当局的注意力,直到奥巴马任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可能对其在亚洲霸权构成的威胁。但即便如此,奥巴马及其国家安全团队仍未将中国定位为同等量级的竞争对手或国家安全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延续了前任的设想,认为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后,终将在政治体制上趋向自由化。
随着特朗普当选,局面骤变。特朗普第一任期彻底摒弃了中国会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推行政治体制自由化改革的幻想。这种立场在特朗普“绝不容忍中国超越美国”的强硬表态推动下,彻底重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当局认定,日益强大的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战略威胁。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国防战略》及同期系列对华政策宣言——包括副总统彭斯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讲话——均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具实力且最危险的地缘政治对手”。这一战略判断并未因特朗普2020年连任失败而改变,而是完整延续至拜登政府时代。尽管拜登政府措辞更为审慎,但政策内核一脉相承:其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宣称中国是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且是“唯一兼具重塑国际秩序意图与日俱增经济、外交、军事及科技实力的竞争者”。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团队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其巧妙动员盟国构建对华遏制网络,将竞争维度拓展至各战略疆域,打造出全域“极限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态势。
中美战略博弈的激烈程度、复杂性和危险性,或将远超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不同于当年在经济层面远远落后于美国的苏联,中国是一个真正势均力敌的强劲对手。亚洲地区更是危机四伏,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等热点区域都可能成为冲突爆发的导火索。随着这场大国角逐不断升级,双方都希望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站在己方。
东南亚虽坐拥庞大人口与日增经济分量,却常遭西方大国忽视,而今将成为这场战略角逐的关键竞技场。特别是与美国缔结同盟条约或存在紧密安全合作关系的国家,如菲律宾,立场已显而易见。这些国家坚信美军力量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利于维系和平稳定。冷战期间亲美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普遍通过获取投资和市场准入实现了经济繁荣;而当时选择与向苏联或中国靠拢的国家,如越南,则经历了相对滞缓的发展进程。在冷战时代,苏联在经济领域显然难与西方抗衡。但今非昔比,如今许多东南亚国家认为,中国已具备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实力。
那些尚未在中美之间做出抉择的国家,往往希望“鱼与熊掌兼得”,这种心态其实不足为奇。传统(虽显简化)观点认为:东南亚国家向美国寻求安全保障,而向中国谋求贸易投资与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战略平衡术正引发中美的“不耐烦”——中国希望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而特朗普势将强化与东南亚经贸纽带,部分动机在于为其在亚洲构建的“安保伞”谋求对等回报。
东南亚地区最关键的外交站队问题仍悬而未决。由于东盟十国因其成员国利益诉求各异,始终未能就两个大国形成统一立场。事实上,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分歧过去曾多次冲击东盟团结根基,未来仍将如此。要准确把握该地区的地缘政治走向,更有效的方法是依据各国具体政策选择,逐一审视东盟成员国的战略倾向。
三、倾向演变:东盟战略选择的动态变化
为解析其对华政策取向,本文研究团队考察了东盟国家与中美在五个维度的互动情况: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经济联系、文化政治亲和力(或软实力)以及信号传递(国家公开表态)。每个维度下跟踪4项具体指标,共计20项量化标准。例如在政治外交维度,综合考察联合国投票一致性、双边合作强度、高层互访频度及多边组织参与度;经济维度则分析进出口贸易额、商业协会活跃度、外资依存度等数据。通过整合这些指标,该研究为每个国家计算出0至100区间的倾向指数——0分代表完全倾向中国,100分代表完全倾向美国。根据这一指标体系,得分在45至55区间内的国家可视为成功地中美两大强国间实现了动态平衡。
我们将这一指数称之为“The Anatomy of Choice Alignment Index”(AOCAI)揭示了两大关键发现。首先,当东南亚国家声称不愿在中美间选边站时,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保持观望状态。过去30年战略倾向数据的均值分析显示印尼(49分)、马来西亚(47分)、新加坡(48分)和泰国(45分)是成功的“平衡者”,始终致力于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而其他东盟国家则呈现出向某一超级大国靠拢的倾向:菲律宾(60分)明确靠向美国,缅甸(24分)、老挝(29分)、柬埔寨(38分)、越南(43分)和文莱(44分)则与中国保持一致。
其次,将30年数据拆分为15年为一周期的两个阶段(1995-2009年与2010-2024年),可以清晰呈现“中国稍占上风”的动态变化图景。以印尼为例,其第一周期的倾向指数为56分(偏向美国),而第二阶段降至43分(偏向中国),中国方面增加了13分。该国从边缘上倾向于美国阵营转变为边缘上倾向于中国阵营。泰国在2009年前尚属坚定的中立者(49分),但此后明显向中国倾斜(41分)。即便是作为美国条约盟友的菲律宾,尽管仍属美国阵营,其指数也从第一阶段的62分微降至58分,显示出对华关系的谨慎改善。马来西亚(49降至46分)与新加坡(50降至45分)同样出现轻微亲华转向,不过仍维持在平衡区间。柬埔寨(42降至34分)、老挝(33降至25分)和缅甸(24降至23分)则呈构建对华友好的稳定网络趋势。唯一呈现轻微亲美趋势的是越南(41升至45分)。我们近期测量的数据表明,越南即将加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行列,在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四、进退维谷:东南亚的战略摇摆
东南亚国家向中国靠拢的趋势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国内政治需求、经济机遇认知、美国的影响力及地缘现实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内政治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柬埔寨便是典型案例。1997年政变最终使洪森掌权,尽管这一事件导致柬美关系急剧恶化,但中柬关系则有所改善。美国在谴责政变“破坏民主”后,中止对柬援助并实施武器禁运。2010年代,美国又持续谴责柬埔寨的人权与腐败问题,这种做法使洪森政权将美国视为政治安全的威胁。因此,柬埔寨选择强化对华关系不足为奇,因为它从中国获得获得了多种形式的支持,且很少受到批评。中国不仅提供大量投资、政治支持与军事援助,也不寻求动摇其政权的合法性。
东南亚多国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在于能否创造强劲经济实绩。这恰恰为中国创造了战略机遇——如今中国已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贸易占比超20%)。东盟内部非民主政体普遍认定,中国既能最大限度满足其经济发展需求,又能助其巩固执政根基。在东南亚外国直接投资(FDI)领域,中国虽暂落后于美国,但通过“一带一路”框架下全球基建项目的资金融通,已在多个国家实现快速赶超。
此类投资正促使多国重新审视其传统世界观。以印尼为例,冷战期间印尼军方对中国充满戒心而向美国靠拢——上个世纪60年代针对华裔群体及所谓“涉嫌亲共”人士的大规模屠杀,便是这种立场的极端体现。但近几十年来,新兴政治精英与商业集团成功推动了以增长为导向的议程。他们将中国视为经济机遇而非意识形态威胁,并通过多重举措引导本国向中国靠拢,如大规模引进中国投资、开展高层互访(如2024年新任总统普拉博沃将中国作为首访国,2025年5月李强总理进行回访)、参与中印尼联合军演,以及避免将印尼华裔作为印尼经济困境的替罪羊等。
特朗普重返白宫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和经济承诺的担忧。其第二任期似乎决意将欧洲防务责任完全转嫁给欧洲各国政府,而在对华及亚洲整体战略上仍显模糊。在安全领域,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三月访问菲律宾与日本的行程表明,美国仍致力于巩固其亚洲同盟体系,并首先从该地区最坚定的两个盟友着手。当菲律宾与中国陷入南海争端之际,赫格塞思声称美对菲承诺“坚如钢铁”。然而,作为另一美国正式条约盟友的泰国却未列入其访问行程。若基于对泰国向中国靠拢趋势的理解,以及美国阻止这一趋势的利益考量,更明智的策略本应安排赫格塞斯访问曼谷。
美国的其他战略伙伴也正密切关注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如果它们认定美国可能从该地区撤军,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重新调整对美安全依赖与合作模式。2017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曾对特朗普政府释放可能削减海外承诺的信号表示忧虑,他呼吁美国重新考虑缩减亚太投入的计划,否则东盟需为承担更大安全责任做好准备。在2025年4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更直言不讳地指出,“新常态”将是“美国从其作为秩序维护者和世界警察的传统角色中退出的时代”,但尚无任何国家准备好填补这一空缺,因此,“世界正变得更加碎片化和无序”。特朗普认为,美国军事力量的投射更多用于保护盟友而非美国本身,这种观点令东南亚部分国家感到不安。新加坡时任国防部长黄永宏今年2月更尖锐指出:美国在该地区的形象已从“解放者”转变为“重大搅局者”,如今更是沦为“索要租金的地主”。在2025年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美受挫后,一位常驻美国的东南亚资深外交官半开玩笑地说到:“乌克兰能提供关键矿产资源,那我们有什么?”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于四月初对东南亚国家征收高额“对等”关税,尽管该政策暂缓实施且前景未明,但这一威胁已然成为笼罩地区经济的阴云。东南亚各国不仅担忧将丧失美国投资与美国市场准入,更忧虑美国放弃其经济领导地位,即将塑造区域经济格局的历史角色拱手让人。若美国在在经济和军事上明显撤出该地区,东盟十国将不得不深化相互依赖,并与澳大利亚、日本及韩国建立更紧密联系。但这种必要性可能会被向中国靠拢抵消。
从根本上说,地缘因素决定了着这些国家的战略抉择。与中国接壤的老挝、缅甸和越南等国,自然会倾向于向华靠拢。诚然,历史因素可能削弱这种引力,如1979中越战争。然而,地缘邻近也可能促使各方做出妥协: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政变夺权后因外交与贸易需求而对中国形成依赖。老挝几乎完全依赖中国资金建设境内湄公河梯级水电站,中国基建贷款已占该内陆国外债总额半数。地缘现实同样解释了越南为何对美关系始终谨慎推进,尽管美国政府公开宣称希望将美越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级别,越南却迟至2023年才同意,这距其与中国建立同等关系已过去15年。无论美国军事基地网络如何广布,其距离东南亚地区的地理距离始终无法消弭。而且一旦南海局势恶化,美国更不可能投入资源和人员来维护和平与稳定。
五、“让出舞台”: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收缩
尽管东南亚整体显然正在倾向中国,但各国的战略取向并非一成不变。各国依旧可以迅速改变立场。菲律宾便是典型例证:2001-2010年阿罗约总统执政时期,该国明显向中国靠拢;而阿基诺三世接任期间(2010-2016年)则迅速回调至亲美轨道;随后的杜特尔特政府再度摆向中国;现任总统小马科斯又重新转向亲美路线。
在印尼、马来西亚等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东南亚国家,美国对以色列加沙战争的支持已引发强烈民愤,促使这些国家政府疏远美国,并对美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说辞表示怀疑。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2024年的调查显示,半数受访者认为东盟应选择中国而非美国,而仅仅一年前,倾向美国的比例还高达61%。
许多东南亚国家政府或许尚未意识到,它们实际上正在选择性地站队。由于这些国家同时与两大强国保持往来,它们自认为其外交政策经过精心权衡,可以在两国提供的战略菜单上各取所需:可以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经贸框架,也能参与中国主导的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同时,它们本有机会加入美国主导(现已夭折)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参与新近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等旨在制衡“一带一路”的倡议,更始终对美国私营部门投资敞开怀抱。事实上,美国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已超过其对中日韩三国投资的总和。通过这样的选择,某些国家可能在不经意间越过边界,最终无意识的站队某一阵营。例如,印尼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密——这并非源于有意识、有条理且宏大的战略选择,而是因为其在不同领域做出的选择(如加入中国主导的各项多边倡议)的累积效应,最终可能使其不可逆转地向中国倾斜。
"Many Southeast Asian governments may not recognize that they are, in fact, taking sides. Because they maintain ties with both superpowers, they assume that their foreign policy is finely calibrated and balanced. They pick à la carte from American and Chinese offerings. "
即便中国崛起而美国退却,东南亚国家也不愿与美国政府划清界限。多项民调显示,东南亚国家虽将中国视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与战略力量,其影响力远超美国。然而,民众对中国如何运用这种力量也抱有相当大的保留态度。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2024年的民调表明:当被问及信任谁时,东南亚各界精英将日本列为首选,美国次之,欧盟位居第三,而中国位于第四。换言之,尽管中国将继续成为美国持久而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似乎正向中国靠拢,但是中国仍需付出巨大努力来消除疑虑、赢得该地区国家的真正信任。
若特朗普政府维持现行强硬路线——包括4月2日对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东盟关键国家实施的惩罚性“解放日”关税未大幅下调、美方要员持续缺席东盟年度峰会、且对已加入(印尼)或申请加入(马来西亚、泰国、越南)金砖机制的国家落实100%关税威胁——中国或将在东南亚赢得更多战略空间。倘特朗普政府不改弦更张,则无异于亲手葬送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在东南亚积累的战略信任与外交遗产。
本文译者
吴雨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学生助理。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
周宇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IIA学术编译组成员。
GBA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