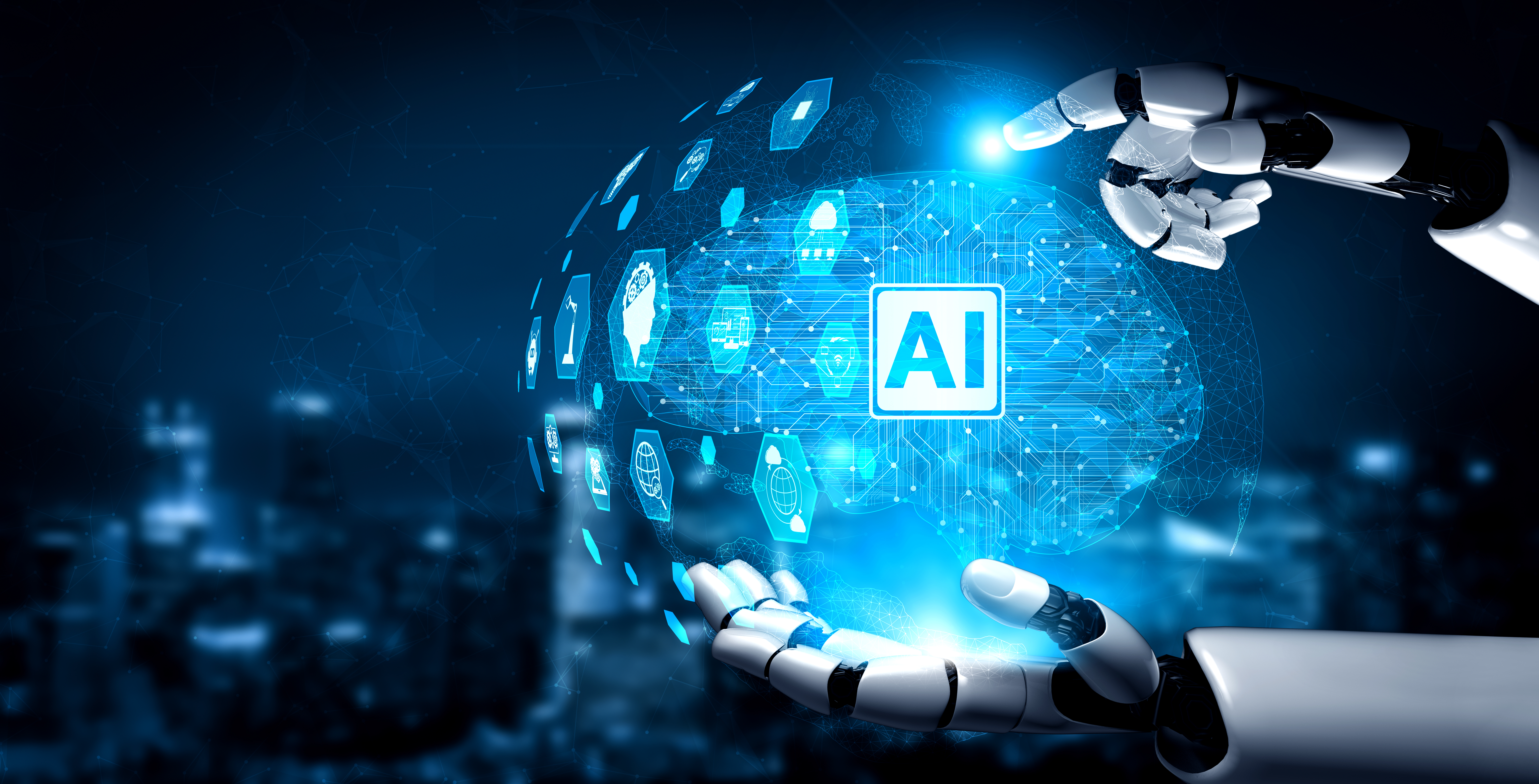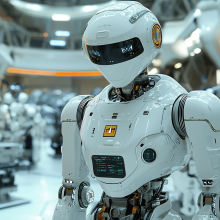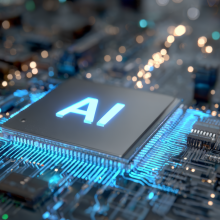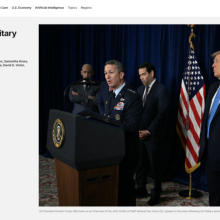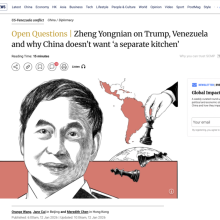编者按:当AI从“工具”蜕变为“另一种人类”,人类正站在通往“人工智能社会”的新路口。在本期对话中,郑永年教授指出,AI革命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存在本质差异:它不仅替代体力劳动,更吞噬脑力空间,将人类推向“整体被取代”的深渊。从“赋能”到“去能”,技术正以算法为牧鞭,驯化出丧失思考能力的“人工智残”群体;而在“羊圈社会”的阴影下,少数技术垄断者与多数“被圈养者”的鸿沟将撕裂文明根基。
面对这场终极危机,我们该如何去做?郑永年呼吁,人类需放弃对AI的“帮手幻想”,以“另辟蹊径”的竞争姿态开辟新疆域——唯有重新分工,才能避免人类在技术奇点中沦为历史的尘埃。这场对话不仅是对未来的预警,更是一封写给人类智慧的求生指南。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冯箫凝
对话时间:2025.07.21
大湾区评论:
近期读了您的新作《AI时代中国的知识重建》,其中有很多关于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探讨,非常深刻。近来,AI的发展正在推动全球性的裁员浪潮。今年全球有141家科技公司裁员超过6万名员工,其中微软大裁员6000人。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既有赋能社会的巨大潜力,同时也对社会秩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冲击。您如何看待这种冲击?
郑永年:
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当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要意识到,我们现在讨论的人工智能,属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说“第四次技术革命”。在此之前,人类已经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所说的大部分工业革命,也就250多年,还不到300年。在之前的几千年历史都是漫长的农业社会。即使在农业社会,也有一些技术发明,比如“牛耕”,犁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发明,它对农业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总体看来,每一次技术发明或者改进都是对人的体力的解放,或者说对“肌肉”的解放。
因此,每一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尤其是就业。比如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原来需要100个农民做的事情,在某项技术发明之后,可能只需要10个人就够了。一方面,我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为新技术的产生,我们人类不用做那么辛苦的体力活了,并且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其他90个人去做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人类历史上已经走过好几次了,并且到目前为止都比较顺利地化解了。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人工智能这一次技术革命对人类的影响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马斯克也说过,以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量可能会大大超过人类的人口数量。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或者说,已经在一些领域发生了。
现在一些人工智能专家,像Geoffrey Hinton(辛顿)他们,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关注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深刻影响。尽管以前的技术对人类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比如就业,但主要还是“赋能”——也就是减少体力活动。技术对人类的“赋能”当然是没问题的,是受欢迎的。但是现在,AI开始对人类“去能”了。你刚才提到的就业影响,将是史无前例的。以前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想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生产效率。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把人从他(她)所从事的工作中“解放”出来那么简单了——不仅仅是体力劳动,可能脑力劳动也要被“解放”出来了。如果那样,我们人类可能需要重新定义自己。
现在很多人认为,可能一些工作例如管道工、扫地工暂时不会被替代,所以,也不用过于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但事实不是这样。大面积的清扫工作是完全可以被机器替代的,即使管道工也是可以被取代的。因此,以前我们面临的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即某些工种可以被机器替代,以提高我们的效率,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被整体取代”的问题,人类第一次面临“整体被取代”的风险。要考虑到,我们今天依然处于“窄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但人工智能发展异常迅速,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
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不懂,但从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我个人对此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整体被取代”的风险。这种取代,不仅仅是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面首先讨论的不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而是“人工智残”(Artificial Ignorance)。当我们在智力上都能被取代的时候,人该怎么办?人类如何重新定义我们自己?
人跟动物,跟所有其他生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认为自己能够进行足够理性和复杂的思考。当然,也许很多动物也有理性思维,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工智能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动物的认知,因为人工智能脱离了语言的限制。为什么说维特根斯坦对人工智能的产生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主人,其他生物都是低等的。我们人类表达意义的方式主要是语言和文字。但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语言本身是有边界的,对那些你不能表述的东西,你只能保持沉默。
人工智能的产生就是受此启发,它观察的是各种行为。现在的人工智能不仅仅是语言大模型,还包括声音、图像等,各种行为模式都可以被用来表达(人、动物或者其它想表达的)意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动物——比如狗、牛、猪,它们的行为模式如果能被找到规律,我们对它们的认知也可以加深。
这当然是人工智能“赋能”的方面,即帮助我们去在更大范围地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但是,人工智能的革命跟前三次工业革命完全不同。前三次工业革命,我们创造的是工具,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它不会反过来影响我们自身,只是将我们从部分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人工智能,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另一种人类”,它也会创造知识,甚至创造人类没有能力创造的知识,创造的效率也远比人类高,并且它创造的知识会反过来影响甚至重塑我们(人类本身)。
我之所以悲观,是因为我觉得人类可能已经出现了“牧民社会”结构。这个社会里,你不仅仅是没有工作可做,你甚至连思考都不需要了。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人”,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如果有一天,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不需要了,我们该如何来定义“人”呢?
我们甚至会退化。现在很多学生已经开始依赖ChatGPT了。这种问答式的工具,其表现已经不比一些人差了。未来社会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少部分人越来越聪明,而大部分人则越来越“智残”,甚至丧失了思考能力。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练习写字,能写出几千甚至上万个汉字。但经过几十年用电脑打字后,现在提笔可能就忘了某个字怎么写。尽管这只是表现为手的技能被忘掉了,但实质上一些字已经从思维记忆中抹去了。如果以后人工智能一直帮你思考,你自己的思维能力也会退化。这个现象我们不可以忽视。
我们要意识到,尽管我们总在讨论“AI and Society”(人工智能与社会),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是“AI Society”(人工智能社会)了。就像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一样,我们已经身处人工智能社会之中。你已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人工智能的现代社会。
只是现在人工智能的巨大影响,我们很多人不仅看不出来,还以为是正常的,因为人工智能大多在后台运作,我们看不到。但其实无论是看手机、用电脑,(每个人)衣食住行的背后都有人工智能在操作。如果有一天它走到了前台,你高度依赖它,以至于自己不会思考了,那该怎么办?当然,有些人觉得人工智能没什么了不起。对于很多年纪较大的人来说,可能确实如此,因为他的前半生是在一个“人工而非智能”的时代度过的。但对新一代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类人”的存在,已经出现了,你不能忽视它。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远远不只是失业的问题。大规模的失业在今后几年一定会发生,这一点大家基本没有否认。即使是现在还处于“窄人工智能”阶段,通用人工智能(AGI)还没到来,它对我们的冲击已经非常巨大了。如果真如人工智能理论所预见,发展到了通用人工智能阶段,人类可能就要“靠边站”了。而到了超级人工智能(ASI)阶段,人类可能基本上就终结了。如果我们人类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取代了,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深刻地分析这个问题,不能光讲发展。
大湾区评论:
2014年,您曾在《技术赋权》一书中以中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那时您给出的结论相对来讲比较乐观,认为技术工具可以有普遍的赋权功能,既能赋权政府,也能赋权社会各个群体。现在您对这个看法是否有改变?
郑永年:
当然有很大的变化,非常大的变化。如果从现在的角度看,我会说互联网是很危险的,人工智能更是危险的。以前我写那本书的时候,互联网和“防火墙”(Great Firewall)时代,基本上是在微博时代写的,那时候技术对人的赋能作用确实比较多。但是,问题不在于技术进步得太快——技术当然进步得非常快——而是我们人类进步得太慢了。对大部分人来说,“去能”的效应现在已经大于“赋能”的效应了。
人工智能现在进步得非常快,各种大模型层出不穷,比如现在的语言大模型。当然,我不是专家,但我看专家们的分析,也觉得虽然各种模型现在有它们的局限性(limitation),但是很快就会有新的技术路径出现,你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在技术层面,所有的可能性都是开放的(all possibilities are possible)。
所以,我个人现在看来是比较担忧的,未来我们如何与人工智能和平共处、共同生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技术进步非常快,但我们人类的“去能”也非常快。这种赋能可能对少数有意识的人还行,比如像马斯克这些人。但我担心的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
大湾区评论:
是的,在AI的发展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您怎么看待这种随着技术赋能(或去能)愈加巨大,而导致社会呈现出更大的不平等和不均衡的现象?
郑永年:
人工智能无论是赋能还是去能,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人工智能为什么“去能”那么快?是因为很多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人,通过各种算法推送,利用了人性的弱点,把人性的最恶劣、最堕落、最平庸的基因给放大了。西方人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但现在的虚拟世界趋向于“魔鬼”当道,全世界都是如此。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延伸。现在所谓的中美竞争,真的是两个国家在竞争吗?还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在竞争?这背后有资本的推动力。我们说平台经济,但平台经济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还是人创造的,就像人工智能是“先人工,后智能”一样。经济也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当然,现在也有人担心人工智能真的会超越我们人类。我刚才也说了,如果到了“超级智能”的阶段,人类确实会有大麻烦。但至少到现在为止,问题实际上还是出在人与人之间:是控制人工智能的那部分人,与被人工智能影响的那部分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还是一种不平等。只是说,以前的不平等更多表现在物质层面或生活水平上,那么以后,如果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智力层面,那就很麻烦了。很多人会变成被圈养的“羊”。
现在这个趋势在很多社会已经出现了。有些工作也不用很辛苦,反正人工智能会帮你干。你就被养着,不用思考。你想要什么、吃什么,物质层面会非常丰富,也不用再做苦力了,就这么活着。如果这样,以后人和其他的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在一个“羊圈社会”里,人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湾区评论:
如您所说,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基本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对人本身的层面,也就是“人工智残”现象,即人类自身的智能可能会越来越退化。第二个是对社会整体的层面,也就是“牧民社会”“羊圈社会”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已经身处AI时代的我们,应该如何去阻止“人工智残”和“牧民社会”这种趋势?
郑永年:
客观地看,因为各个社会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阶段不一样——有的落后社会可能还没大量接触到人工智能,而像中国和美欧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我们的生活了。情况不同,我们还需要观察。
首先不能说“我不要人工智能了”,这一技术已经产生了,我们肯定是要去拥抱它的。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都拥抱了人工智能。在学术界,今天流行“AI for Science”和“AI for Social Science”表明人们已经在拥抱人工智能了。很多人说,以后人类只有两种:一种是会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另一种是不会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即使这个判断不完全成立,但所有的人都会被人工智能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哪怕你不主动去使用,你也在被动地使用,因为它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当然,大家以前讲“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基于基础设施等因素。但未来,无论你有没有(主动使用),都会受影响。因为人类以后所获得的信息,大部分都将是人工智能制造的。以前,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人把自己创造的知识放到互联网上传播。现在,互联网上的内容已经变成一部分是人创造的,一部分是人工智能合成的。而且,人工智能创造知识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内容越来越多,可能没多少年,80%至90%的内容都是人工智能创造的,并且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是机器创造的。我的估计是,5到10年内,互联网上大部分的知识都将由人工智能生成。到那个阶段,比如一份由实体乙方写的方案和一份由人工智能写的方案,你可能根本分不出来。甚至人工智能写的可能比乙方自己写的还要“乙方”。到这个阶段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都将成为人工智能高度影响下的一部分,它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不可能把这个技术毁灭掉,技术产生了就是产生了,我们只能拥抱它。
那么,人类怎么办?我们人类要另辟蹊径——我们必须强调,人工智能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另外一种人类”,我们只能和它进行劳动分工。
你要去看,我们人类现在在做的哪些事情,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做了,而且它的效率比我们高,以后肯定会被它取代。这些事情,你就不应该再去做了,至少要考虑不去做了。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所以要去寻找新的东西,看你能做什么。
现在很多人的思路还是不对的。有很多人说,管道工这类工作人工智能可能替代不了。但你看,现在爬电线杆、检测铁路桥梁,这些都是人工智能能做的事情。以后角落里的管道维修,它照样也能做。
人类作为到目前为止的“高级智能”,你只能去开辟新的疆域。就像马斯克觉得地球不够了,要到火星上去一样。比如我们做学术的,就要看哪些知识领域是人工智能所不能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开始寻找新的工作——而新的工作,说不定对我们人类还是有益的。我们要跟人工智能竞争,要有一种竞争的心态,而不是依赖,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帮你干活的帮手。
前面三次工业革命,技术都是我们的“帮手”。现在我们很多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帮手”这个概念上。如果只看到AI“赋能”这一面,把它看作帮手,你明天就可能会面临失业。所以,我们现在面对人工智能的决心还远远不够,你要有“另辟蹊径,占山为王”的态度,把某些领地让给它,然后去开辟我们自己的新领地。只有用这种态度,我们才能应对今天人工智能带来的紧迫挑战。
GBA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