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外資和民資為何「躺平」? 如何面對中國營企業所面臨的困境? 國際層面的因素一時三刻很難改變,能改變的就是我們自身內部的要素。 就內部要素而言,重振經濟迫切需要解決三大核心問題,即權利、空間和手段。
Facts | Insight | Impact
獨思錄
Thinking
Alone
Prof. Zheng Yongnian
鄭永年
03.08.2024
第03錄
編者按
外資和民資為何「躺平」?
權利、空間、手段──解決企業家的三個核心問題才能更好的面向未來。
就權利問題而言,企業家和企業的權利核心在於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 這兩個權利的保障對於企業家的發展動機至關重要。 資本的原始累積、政商關係中的官員牽連等問題影響這些權利的實現。 就空間問題而言,在規制型市場經濟,企業的空間會受到諸多限制,國家會限定企業參與部分被認為不可接受的經濟活動。 而中國企業的空間更具有特殊的背景。 就手段而言,手段問題主要指向金融,應主要透過金融體制改革來為企業“松綁”,並應考慮到醫療、教育和住房等領域的社會屬性多於經濟屬性。
如何面對中國營事業所面臨的三大困境? 鄭永年教授在本篇文章中給了他的思考和可行性方案。
2022年黨的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與目標。 2023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品質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透過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作為政策主體的政府和作為經濟主體的企業家之間的合作。
為此,政府在動員企業有所作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就外資而言,我們不斷強調開放的重要性,聚焦於圍繞制度型開放的高水平開放,加大了從高層到民間資本「走出去」和西方世界溝通的力度。 就民資而言,中央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的31條,強調“兩個毫不動搖”,最近各方面也在加快《民營企業促進法》的製訂。 同時,各地也根據地方情況推出了更多的條例。

山東鄒平魏橋輕量化基地宏奧全鋁車身整合生產車間(圖源:新華社)
但從企業的行為來判斷,我們依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無論是民資或外資,「躺平」「不作為」「無可作為」仍是「現象級」現象。 經驗地看,外資流出還是一個趨勢,至少就統計而言,外資流出比進入的多。 創投領域的外資幾乎消失了。 民資的情況也不樂觀,除了新能源領域和進口替代的幾個領域外,固定資產投資方面民資不僅躺平,而且在減少。
經驗地看,不難發現,外資和民資的「躺平」是兩個互相關聯又有區別的現象,各自的「躺平」有各自的原因,也有一些共同的原因。 整體上,無論是外資或民資,「躺平」既有包括地緣政治、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等國際因素的影響,也有中國本身的一些內部因素的影響。
國際層面的因素一時三刻很難改變,能改變的就是我們自身內部的要素。 就內部要素而言,重振經濟迫切需要解決三大核心問題,即權利、空間和手段。
01 論權利
權利指的是經濟主體企業家和企業的權利。 企業家和企業有許多權利,但權利的核心是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 這兩個權利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古今中外,不管在什麼樣的體制下,如果這兩個權利得不到保障,不僅不可能產生企業家,而且企業家沒有任何的企業發展動機。 很可惜,有些人往往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兩種權利,把它們視為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權利。 這種看法並不符合實證。 這兩種權利,與其說是“權利”,不如說是“人性”。人性的本質是趨利避害。 如果企業家所創造的財富甚至其生命得不到保障,那麼就沒有任何人會去創企業、圖發展。 如果一個經濟體係是從這一人性出發來設計的,那麼其經濟就可以得到發展;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系的設計不能保障這兩種權利,那麼經濟必然是落後的。 這已經被大量的經驗證據所證實。
在保障這兩種權利方面,企業家和企業面臨幾個主要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新鮮,但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並且不時地會回來困擾企業家和企業,甚至影響到企業的生存。 經驗地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資本的原始累積問題。 發展需要資本,而資本的累積總是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在任何社會都是如此。 馬克思對西方原始資本累積的批判到今天仍然不失其有效性。 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和處理原始累積這個環節。已開發國家在這方面處理得比較好,除了懲罰那些「罪大惡極」的資本行為之外,透過立法促成了企業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企業家除了用所累積的資本實現企業的永續發展之外,把大量的錢財用於設立基金和慈善,而後者也已經成為社會發展所必須。 例如,在美國,最好的私立大學和最好的智庫都來自企業和他們所設立的基金。
比較而言,我們對企業的原始累積問題還沒有找到各方都可以認同的認知,更沒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來處理。 如果人們用今天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去看待以往的企業家作為,那麼大多作為都可以被視為“不合規”,甚至“不合法”的。 這個問題始終存在,不同官員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有時不那麼重要了,但有時又變得非常重要。 這取決於官員本身的裁定,表現為「隨意」。 對企業家來說,這個問題隨時都可以回來,演變變成財產安全甚至是生命安全問題。
第二,企業家和官員的牽連問題。 這些年來,黨和政府大力反腐,強化治國理政建設,這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主體所必需。 但是,因為中國特殊的政商關係,黨內反貪腐往往牽連出許多企業家。 中國政商關係的特殊性在於,這種關係不是政府作為一個實體和企業作為一個實體之間的關係,而是官員個人和企業家個人之間的關係。 現在的情況是,所牽連的企業家也受到同樣的懲罰,諸如「留置」「異地審判」等用於官員的方法也普遍使用於企業家。
中國的經濟從來是「兩條腿」走路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都很重要。 現在的情況是,政府官員和企業家互不信任,失去了聯繫和接觸。 儘管兩者都迫切希望建立一種「親清」關係(親商但清廉),但不知道如何確立這種關係。 原因很簡單,因為這種關係的確立需要政商關係從個人關係轉型為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而這種轉型需要製度性改變。
第三,企業家和企業的關聯問題。 在世界範圍內,對第一代企業家來說,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但之後就會產生企業家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問題。 在西方,隨著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法律法規隨之配合這種變化。 因此,即使企業家出了問題,其所屬的企業不會出現問題,照常運作。 但我們還沒有這方面的任何經驗。 整個社會甚至企業家本人都不會對企業和企業家作任何的分離。 因此,企業家出現了問題,整個企業都受遭殃;企業出現了問題,企業家也同樣受遭殃。 這種關聯性使得企業營運成本異常地高。 這些年,基本上企業都是隨著企業家的崛起而崛起,隨著企業家的倒下而倒下。
第四,社會環境問題,主要表現為社會對企業家和企業的認知問題(這個問題會以另文討論)。 簡單地說,社會對企業的認知構成了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文化環境,偉大的認知孕育偉大的企業家和偉大的企業,而平庸的認知孵化平庸的企業家和企業。

3月3日下午,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記者會舉行,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成兩會熱點(圖源:新華社)
02 論空間
如果說財產權和生命權關乎企業家「為什麼要做企業?」的問題,那麼空間就關乎企業家「做什麼?」的問題。 不同國家和不同體制,企業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空間問題。 在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企業的發展空間幾乎是無限的。 如果說企業面臨空間問題,那麼這些問題都是由技術發展程度等經濟要素決定的。 但這種完全自由市場僅存在於原始資本主義時代,現代社會已經沒有完全的自由市場——即使像美國那樣被視為自由主義模板的經濟體,儘管在企業發展早期很少有其他因素的干預 ,但等企業成長起來之後,政府也會對企業進行規制。
在規制型市場經濟,企業的空間會受到諸多限制,國家(政府)會限定企業參與那些被認為不可接受的經濟活動,公眾利益、環保、國家安全、倫理等都是被考慮的因素。 一般而言,這反映在西方從早期的「企業的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到今天的「環保、社會與治理」(ESG, 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概念的變化上 。 今天,地緣政治和經濟民族主義等要素對企業運作空間構成了越來越嚴峻的限制。
中國企業的空間更具有特殊的背景。 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在發展規制型市場經濟。 但較之其他規制經濟,中國往往出現過度監管的情況。就發展和監管而言,中美剛好構成兩個極端。 美國是發展導向的,先發展後監管,而中國是監管型的,還沒發展起來就擁有了監管條例。 現今的高科技領域就非常具有典型意義。 儘管美國各方面一直在呼籲監管,但迄今並未出現有效的監管體系。 在這個領域自生的體系確立之前,政治不會介入,更不用說是確立技術倫理(ethics)了。 相較之下,中國在這個領域已經發展出強監管體系。
除了規制型市場經濟下企業所面臨的空間問題之外,中國企業的主要限制因素來自混合經濟體製本身,即國營企業的存在這一事實。 國營企業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核心,這產生了國企和民企的空間分配問題-空間分配是動態變化的。 在1990年代,中國推動大規模的民營化,成功實現了從計畫經濟到市場導向經濟的轉型,民營企業空間大增。 國營企業分佈在自然壟斷、公共服務和國民經濟的支柱領域,而大多數競爭性領域讓渡給了民企。 也就是說,國企是有產業和領域的,有邊界的。 但之後,國企往往大規模衝破原來的邊界,向民企領域拓展,造成了民間所說的「國進民退」局面。 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企大肆侵入原來屬於民企的領域。 近年來,國企又從原來的“管業”演變成“管資本”,這導致了“哪裡有錢賺,哪裡就有國資”的情形,形成了國資與民(企)爭利的局面。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因為地緣政治和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等因素的影響,外資進入減少,民資不活躍,而國資(尤其是地方國資)因為承擔著“穩步增長”的責任,呈現不得不活躍的 局面,這一方面導致了經濟領域的“內卷”,另一方面則導致了民資空間的繼續萎縮。 原本民資佔「56789」(即整個經濟體中,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毛額、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 %以上的企業數量)的局面正在迅速改變。
事實上,在現今的科創領域,即使在中國孵化的企業,也往往因為找不到發展空間或沒有足夠的空間,而轉移到國外發展。這無疑是中國的損失。 這與美國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例如,在美國矽谷,高達三分之二的「獨角獸」是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所有。 「美國製造」並非美國人才製造,而是世界人才創造。 這表明,越來越多的企業,包括中國的企業在美國找到更適合自身的發展空間。

圖為美國矽谷(圖源:Getty Image)
也要強調的是,就空間而言,外資所面臨的問題和中國民企所面臨的問題具有同樣的性質,即缺乏空間。 外資進入中國之後,要不獨自發展,要不和民企結合發展,很少和國企合作(除了早期的汽車業)。 因此,民企遇到了困難,外資也同樣遇到了困難。 西方資本一直在抱怨中國的開放度不夠。 無論從理論上或經驗來看,在不能對民資開放的情況下,對外資的開放會變得更加困難。 同樣,如果要向外資釋放出更大的開放訊號,那麼首先就要加大對民資開放的幅度,給民資更多的空間。 這還不夠。 更重要的是,要從法律和法規層面規定國企的邊界。 重新回溯像1990年代對國資那樣謹慎的思考,變得特別重要。
03 論手段
手段問題關乎企業家「如何做?」的問題。 在任何社會,手段問題主要指的是金融問題。 在美國,金融市場最發達,各種金融工具共存。 在當代,一個重要的改變是供給面革命,即從前是企業向金融機構融資,而現在是金融機構孵化企業。 最典型的是在高科技領域。 高科技領域風險大,回報也高。 政府不能進入如此高風險的領域,因為政府的錢是納稅人的錢;傳統的銀行也很難用存款人的錢進入高風險領域。 因此,二戰之後,美國發展出了創投業,把社會上願意進入高風險領域的錢進行高風險投資。 今天,越來越多的高科技可以說是金融「砸」出來的。
在中國,金融領域由國家銀行控制,而國家銀行的天然服務對像是國有企業。 儘管中央政府一再強調國營銀行要為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服務,但並沒有形成有效的動力機制,促成國營銀行為民營企業服務。 民企事實上也較少從國營銀行獲得服務。 更糟的點在於,國營銀行給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貸款利率是很不一樣的——給國企的利率很低,而給民企的利率很高,造成了巨大的金融不公。 這種現實也導致了多種形式的「非法」民間融資,因為國有銀行無法滿足民營企業發展要求,許多企業只好轉向其他途徑來融資。 經驗地看,越是民營企業發達的地方,這些另類「融資」方式就越多,政府很難禁止它們的出現和發展。 一方面是國營企業的錢來得太容易、太便宜,阻礙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卻得不到有效的融資,民資的勞動生產力也得不到有效發揮。 這是中國經濟的一種結構性矛盾。
除了融資,中國企業的獲利能力和水準也是一個問題,因為這影響到企業的資本累積問題。 作為發展中國家,製造業的技術一般都是應用性的,也就是對已開發國家的技術的應用。 西方資本帶著其技術進入中國之後,已經壓低了中國企業的利潤率。 在早期,中國企業還可以用本土廉價要素(勞動力、土地和較低的環保要求)尋得較大的利潤空間,但隨著本土要素價格的上升,製造業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很多 企業顯得非常脆弱,沒有競爭力。
在手段方面,中國企業也面臨醫療、教育、住房等領域因過度政府監管而無法獲利的局面。 醫療、教育和住房本來屬於社會領域,或者說這些領域的社會屬性大於經濟屬性。 但在改革開放之後的許多年裡,人們對這些領域的社會屬性認知不足,導致了過度市場化的問題。 在不同的時間段,這些領域成為了「暴富」領域,導致了巨大的社會不公平、不公義。 但為了糾正這種現象,近年來的政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過度的政府監管。 在房地產領域,經過多年限購後,現在各地逐步開放限購了,但人們發現房地產的高峰期已經過去。 教育領域的情況並未改變,但因為華人家庭沒有選擇,在正式教育體系中,教育不公的現象仍持續。 教培領域在短時間內得到整頓,但導致了更大程度的不公平。 在醫療領域,因為有健保系統,這個領域的企業的獲利水準要適合中國的醫保水平,這促使領域內的許多企業沒有獲利空間。 如果不能獲利,那麼這些企業就會失去生存的手段。
04 論未來
權利、空間和手段是中國營企業所面臨的三大困境。 權利是大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後兩者不會發生;同時,即使有了權利,如果沒有後兩者,那麼企業行為很難產生和發展。 對中國來說,唯有改革,尤其是體制層面的改革,才能從根本解決問題。 如同以上所分析的,改革的出路也是很明顯的。 概括地說,如下十個方面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確立正確的企業責任敘事。 企業承擔著本身的發展責任、對社會的社會責任和國際層面的國家責任。 儘管中國已經形成了混合所有製,在法律法規政策等層面,對不同所有權企業也作了諸多解釋,但迄今並沒有系統的、學理和法理上的敘事。 正確的企業敘事能幫助全社會對企業有正確的認知,創造有利於企業發展的社會文化環境。
第二,盡快解決企業的原始累積問題。 這個問題是一直存在的,政府並沒有一個統一和最終的說法,都是因人而變、因時而變,為企業家和企業製造了巨大的不確定性。 可以以法律或決議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得越早,對企業的發展越有利。 這個問題的解決是保障財產權和生命權的前提,否則企業的發展無從談起。
第三,改革政商關係,解決官員和企業家的牽連問題。 現在問題的產生是因為政商關係表現為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個體之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容易產生腐敗。 從短期來看,要把兩個群體區分開來,不能把懲罰官員的方法簡單地適用到懲罰企業家。 從中長期來看,要透過體制面的改革,把兩者之間的關係轉化成為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即政府作為一個實體,和企業作為一個實體。 已開發國家早已解決了這個問題。 並且,在現代資訊科技條件下,這個問題不難解決。 中國香港、新加坡等不少經濟體早已解決這個問題,實現了政商之間交往的“無人化”,即幾乎不用通過人際交往的方式來完成。

政府搭台民間唱戲,打造港式「夜經濟」(圖源:香港文匯社)
第四,企業和企業家的分離。 企業家一出問題,企業就出問題,反之亦然。 這種情況不僅是企業的損失,對社會帶來的代價也過大,因為企業不僅是企業家個人的事情,更涉及員工及其家庭問題。 從短期來說,政府在處理兩者時,迫切需要把兩者分離開來,實事求是地處理問題,盡可能給企業生存的空間。 從中長期來說,要透過立法等形式促成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也就是家庭家族企業的轉型。 實際上,家庭家族企業的問題已經提到許多企業的議程上來了,但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可以總結。 這方面,需要虛心向已開發國家學習,否則解決不了「富不過三代」的問題。
第五,國營企業和國資的邊界。 國營企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正因為其重要性,國營企業必須限定在重要的領域,如自然壟斷產業、基礎建設、國防軍事產業、國民經濟支柱產業。 國企涵蓋的領域越廣,其能力就越弱。 應當回到1990年代國企改革的思路,國企應當「管業」「管領域」。 同樣,國資也需要有邊界,必須避免「與民爭利」的局面。
第六,民企要主導競爭性產業。 在限定國企和國資邊界的同時,要把廣大的競爭性領域讓渡給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的創新來源,必須擁有龐大的經濟空間。 一旦民營企業缺乏空間,那麼國家經濟的創新發展能力就會被弱化。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的持續崛起,中國必然要發展自身的跨國公司。 因為和西方經濟關係趨於緊張,國營企業或國資的國際化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必須承擔建設跨國公司的責任。 但只有在民營企業有足夠競爭力的條件下,跨國公司才有可能出現。 在中國的情況下,法律法規政策要引導企業的向上競爭,而減少甚至避免「內卷」或向下競爭。
第七,在發展和監管之間實現平衡。 美國是發展模式,中國是監管模式,兩者各具優勢。 但正如中國成語「止戈為武」所意味著的,只有當擁有了「戈」之後,才能防禦他人的「戈」的攻擊,實現和平。 至少在高科技領域,中國模式過度強調監管,阻礙了科技的發展。 更好的政策應是:先容許、鼓勵新企業的產生和發展,待其成長一段時間、形成了一個經濟學界所說的「自發秩序」之後,政治才介入,進行規制評估、建立規制體系。 過早的政治介入或道德判斷會過早「殺死」企業。 要意識到,對所有國家來說,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感。 尤其在國際層面,國際政治依然盛行「不在餐桌上,便在食譜上」的達爾文主義原則。 企業是國家經濟能力最主要的工具,更是其他方面競爭力的基礎。 因此,我們的政策選擇應是“發展之上的規制”,而非現在的“規制之上的發展”。
醫療、教育和住房等屬於社會領域或社會性很強的領域,政府必須承擔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以實現基本社會公平,因此不可以過度商業化,強監管是必要的。 但是,必須意識到,強監管並不是說不要市場和取消市場。 我們需要藉鏡新加坡等經濟體的經驗,在政府保障提供大部分居民的服務(例如透過規制的價格)的同時,必須開放一部分給予市場調節,讓市場提供差異化服務。 面前「一刀切」的監管政府無法為經濟主體提供任何動力機制,這種局面不改變,就會導致這個領域的落後,尤其是醫療領域。 保障經濟主體一定的利潤空間是保障他們繼續投入的動力機制。

2022年1月福建省三明市沙縣區總醫院便民門診窗口,群眾在諮詢報銷情況(圖源:新華社)
第八,改革金融結構。 大型國營銀行的結構應當改革了。 中國必須擁有大量能夠服務中小型民營企業的銀行和金融結構,否則中小企業很難發展。 要實現這一目標,政策選擇有幾個:1)建造一大批地區性的中小型銀行和金融機構,專門服務於中小企業;如果是國有的,那麼考核標準應當和大型國有銀行區分開來; 2)容許發展民營銀行和金融機構,來為中小型民營企業提供服務;3)容許國有和民營中小型金融機構的同時存在和發展。
第九,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在獲取金融服務方面的公平性。 無論是國營企業的信貸成本過低,或是民營企業的信貸成本過低高,都不利於經濟效益的提高。 國營銀行對國營企業和民營商的貸款必須公平化。 需要有專門的監督機構監督國營企業所製造的「不公平」。
第十,金融的供給面革命。 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中國本身的創投體系。 較之美國經濟,金融是中國最大的短板。 儘管我們提出了建立「金融強國」的目標,但還沒有金融發展的規劃。 金融發展涵蓋各個層面,而創投體係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今天,從中央到地方,國資在扮演「準風投」的角色。 需要透過行政體制改革,促成國資的長期主義。 現在國資的短期主義,不僅無助於企業的發展,反而「腐化」了企業的競爭精神。 更重要的是,要容許和鼓勵民間風投業的成長和發展。 要把龐大而閒散的民間資本集中起來,投資未來。 在數量型經濟的擴張到了頂點之後,許多經濟活動,尤其是科技類經濟活動,需要透過金融來孵化。 沒有金融側革命,國民經濟就很難從先前的「追趕經濟」轉型成為「前沿經濟」。

關注我們

大灣區評論
事實·洞見·影響
| 原創聲明 |
本文版權歸微信訂閱號碼「大灣區評論」所有,未經允許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轉載、複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內容,侵權必定。 公眾號授權事宜請直接於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權事宜請聯絡IIA-paper@cuhk.edu.cn。
GBA 新傳媒
評論文章
 如何“破局”与“共融”?——百川论坛“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地缘政治与发展合作”2025研讨会在深启幕
如何“破局”与“共融”?——百川论坛“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地缘政治与发展合作”2025研讨会在深启幕 練卓文:加強中歐合作應對當前的國際貿易挑戰
練卓文:加強中歐合作應對當前的國際貿易挑戰 包宏:美元——特朗普發動全球關稅戰的根源、底氣與死穴|經濟觀察
包宏:美元——特朗普發動全球關稅戰的根源、底氣與死穴|經濟觀察 王希聖:從「重新武裝歐洲計畫」到《歐洲防務白皮書》 ,歐洲安全能否離開美國?|戰略與安全
王希聖:從「重新武裝歐洲計畫」到《歐洲防務白皮書》 ,歐洲安全能否離開美國?|戰略與安全 俠客島對話鄭永年:我們要「超越關稅看關稅」
俠客島對話鄭永年:我們要「超越關稅看關稅」 俠客島對話鄭永年:特朗普關稅「休克療法」能醫治「美國病」嗎
俠客島對話鄭永年:特朗普關稅「休克療法」能醫治「美國病」嗎 鄭永年、段嘯林、袁冉東:深圳下一步發展的「三個共識」|全球灣區觀察
鄭永年、段嘯林、袁冉東:深圳下一步發展的「三個共識」|全球灣區觀察 中國和美國拼的是「經濟韌性」|獨思錄 x 鄭永年
中國和美國拼的是「經濟韌性」|獨思錄 x 鄭永年 「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現狀及其未來|獨思錄 x 鄭永年
「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現狀及其未來|獨思錄 x 鄭永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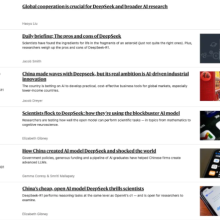 遊傳滿:如何「鉗制」DeepSeek?OpenAI如是說|全球法治觀察
遊傳滿:如何「鉗制」DeepSeek?OpenAI如是說|全球法治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