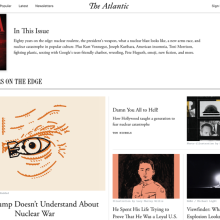编者按:在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技术与数据跨境流动被政治化的当下,亚太正站在“开放还是收缩”的关键岔路口。2026年APEC首次高官会在广州举行,会议把“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大优先事项。郑永年教授在APEC高官会上鲜明指出:开放不是选项,而是前提。开放一旦坍塌,创新就会失去“氧气”,合作也将失去支点。
本文以“开放是大前提”为主线,提出构建竞争性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路径:以基础研究、应用转化能力与服务创新的开放金融体系形成“新三驾马车”,在规则治理与风险管控中推进更有智慧的开放,进而把开放转化为合作、把合作转化为能力;并倡议以互联互通的创新枢纽、要素流动规则协调、教育与人才体系开放等,打造面向未来的“创新能力共同体”。
*本文内容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广州召开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一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2026年2月2日)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APEC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 (PPSTI) 主席及副主席们,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的同仁们,朋友们:
今天能在广州与诸位相聚,我深感荣幸。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广州已经被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重塑。同样,我也有幸在本次对话中阐述一个简明而深刻的理念: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它并非作为点缀,而是发展的基石。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提出三大优先事项:开放、创新与合作。这三者并非口号,而是逻辑链条。开放为先,创新相随,合作方能实现。开放性一旦崩溃,创新便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氧气”;合作也随之失去立足之地。
01 开放:创新、合作与发展的逻辑根基
我希望阐明这样一个核心理念:开放是大前提。没有开放,就不可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系统;没有这样的生态系统,“高质量生产力”将永远停留在愿景层面,而非现实能力。
请允许我从三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创新绝非孤立诞生,而是源于互动碰撞。当不同思想、文化、制度和解决问题的传统相遇时,便会产生化学反应。这种碰撞会催生新想法,带来新思考,创造新工具,孕育新产业。这是现代史中反复上演的模式。开放的社会能激发更多碰撞,封闭的社会则会扼杀创新。即便是曾经在科学上处于引领地位的国家,一旦自我封闭,也会落后。因为创新源泉会枯竭,而人才与资本也不会停留在紧闭的国门内。
其次,开放是合作的先决条件。合作并非“施舍”,而是一种基于优势互补的互利行为。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唯有通过贸易、交流与人员流动,这些优势才能转化为共享收益。没有开放就没有交流,没有交流就没有合作。
第三,亚太地区正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当今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压力加剧。地缘政治压力正在重塑规则体系,技术、数据与人才的跨境流动被政治化。这并非一场短暂的风暴,而是可能持续数年的结构性转变过程。
那么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现实?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护开放性,必须在应当推进之处深化开放,并制度化开放以超越政治周期。
02 开放的中国实践
开放可以和中国的经验联系起来,因为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实践案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奇迹并非源于闭门造车,而是源于开放。开放带来了资本、技术、市场、理念、标准和竞争。竞争迫使学习,学习会推动升级,而升级创造了繁荣。
但发展并非是一直线型的。一个国家可能经历高速增长却仍旧陷入停滞。即便许多经济体摆脱了贫困,却在迈向高收入阶段前停滞不前。人们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1. 如何突破“中等技术陷阱”?
我认为还需引入另一个概念,我称之为“中等技术陷阱”。指的是一种经济体能够大规模生产,但在技术前沿创新时却面临无法持续的困境。经济体有能力组装、改进,但难以创新。而当最领先的技术不断加速发展时,不同经济体的差距便不断拉大。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世界正迎来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生物技术加速推进,能源转型正在重塑产业格局。若经济体持续停滞在中等技术水平,将面临生产率增长放缓、薪资增长乏力、社会压力加剧的困境。
那么,该如何突破“中等技术陷阱”?
我提出了“新三驾马车”理论作为解决方法。国家需三股力量协同驱动:“第一驾马车”是基础研究——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与自由探索空间,没有坚实的基础,便无从实现原创性突破;“第二驾马车”是强大的应用转化能力,需要企业与平台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需要工程人才、试验平台、行业标准和早期市场,这正是我们这次会议所说的“科学发现”或者我们中国所说的“新质生产力”具象化之所在;“第三驾马车”是服务于创新的开放金融体系,创新伴随着风险,需要耐心的资本,需要匹配长期开发周期的融资工具,更需要全球互联,因为前沿创新几乎没有局限于单一国家的情况。这“三驾马车”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正需要开放。
回顾二战后的美国,其科学领导地位不仅源于美国人的智能,更源于开放的教育人才体系、开放的技术体系和开放的金融体系。正是这些开放体系吸引了全球人才、思想和资源的汇聚,才造就了硅谷的传奇。即便全球最强大的创新力量都依赖开放,封闭也绝非通往领导地位的道路。
2. 开放的治理与规则
当然开放并非不存在任何风险。开放也需要治理,需要规则,更需要在维护生态系统的前提下管理安全事项的能力。近年来,世界正经历我曾提过的“有限全球化”。尽管经贸纽带并没有消失,但各经济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可能弱化,关键要素的流动可能变得更具选择性。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个经济体都将面临抉择:是封闭收缩,还是有智慧地进行开放,并协同推进规则标准的统一?
中国选择了后者。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在诸多领域愿意率先采取单边行动。在动荡世界中,中国的市场开放可以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一个保持开放的大市场能稳定预期,并维系价值链运转。
3. 开放的思维方式
同时,开放也关乎思维方式。中国无意颠覆国际秩序,更应被视为“改革者” (reformer) 与“完善者” (supplementer) 。这意味着:尊重现有规则,针对不符合新形势的规则进行完善,减少无谓的妖魔化。相互指责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抬高合作成本。
这种思维方式也具有现实意义。自信的经济体能够吸引人才和资本,大胆开放并有效地管控风险。这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而是战略性的现实主义。
4. 开放与合作
但仅有开放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将开放转化为合作,将合作转化为能力。这就让我们重新回到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的《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 (APEC’s Putrajaya Vision 2040) 呼吁建立开放、充满活力、具有韧性且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该愿景强调创新和数字化是发展引擎。方向很明确,而挑战在于如何落实。
03 构建“创新能力共同体”
在此,我愿提出一项亚太科技共同体 (Asia-Pacific sci-tech community) 的务实议程:我称之为“创新能力共同体” (a community of innovation capability) 。不是集团,而是运作体系。
首先,建立互联互通而非孤立的开放创新枢纽。每个经济体都可培育本土枢纽,但枢纽必须实现跨境联通。我们需要前沿领域的联合实验室、标准试点的联合测试平台,以及让跨境协作成为常态而非特例的创新走廊。
其次,协调创新要素流动的规则。人才、资本、数据和研究工具必须能够流动。若流动受阻,生态系统便无法学习;若无法学习,便失去竞争力。目标应是实现最低限度可行的协调,而非追求完美统一,但需确保足够的兼容性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可从沙盒机制起步,分行业开展试点,再将有效模式推广。
第三,守护教育与人才体系的开放性。这是当下最敏感的领域,亦是最关键的环节。阻断人际交流即阻断思想碰撞,禁止学生共同学习则断绝新生代间的互信。战略性猜疑由此固化,而永久性猜疑终将导致永久性停滞。
第四,构建耐心资本合作机制。可探索针对长周期技术的联合投资模式。共享评估最佳实践,扶持、奖励坚守而非炒作的风险投资,将公共资金与私营纪律相衔接,避免创新沦为资源浪费。
第五,保持务实合作。可从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切入:气候适应、清洁能源、粮食安全、公共卫生、老龄化问题,以及强调安全与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携手解决现实难题,信任自会随之建立。信任形成后,更大规模的合作方能实现。
请容我补充一点: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不仅在于开放,更在于竞争。竞争能规范创新,催生更优产品,提升效率,并保护消费者与纳税人权益。
竞争与合作并非对立。共同规则能减少摩擦,减少摩擦能吸引更多参与者,更多参与者意味着更多创意,更多创意则带来更多创新。这正是生态系统兼具开放性与韧性的原因所在。
请允许我回到开篇的论点:开放是大前提。短期来看,闭门自守或许看似安全,但这实则是虚无的安全感。它会阻碍学习,压缩可选项,并最终扼杀未来。长远来看,开放绝非软弱,而是力量——是吸收的能力,是适应的能力,更是创造的能力。
亚太地区面临抉择:是让反全球化定义未来,还是通过开放、创新与合作,共同建设繁荣的亚太共同体?让我们敞开大门,架起桥梁,完善促进合作的规则体系,将“科学发现”或者“新质生产力”从理念转化为全体人民共享的能力。
GBA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