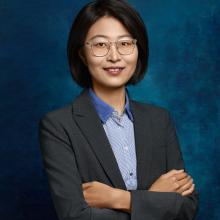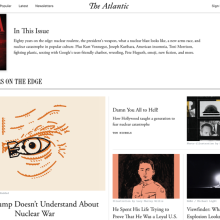编者按:1982年,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提出发展型国家理论,用以描述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凭借“计划理性”的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强国家能力及高自主性,将经济发展确立为首要目标,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切入分析,但强调美国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是与日韩“发展型国家”不同的模式。通过将硅谷科技右翼深度纳入政策过程,特朗普政府出台了高度产业友好、利于前沿科技创新的政策框架,具体举措包括去监管、基础设施建设、联邦层面的数据共享、行业标准制定、政府需求创造以及与业界沟通渠道的建立等。尽管难以否认AI泡沫的存在,但必须承认,这些政策正在开启新一波的产业繁荣。
一项技术能否具有革命性,终究要看它能否深度嵌入于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美国大力发展AI技术背后,是在调动内部及盟友资源以完成自身经济的“再平衡”。对中国而言,既可借鉴美国培育创新的政策举措,也要注意到与美国面临的优先议程的不同。科技竞赛的“零和叙事”并不可取。将AI与产业相结合,将是中国利用这一波技术浪潮实现发展的重要路径。
长期以来,美国被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但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观点不再奉此为圭臬,而是逐渐强调美国通过政府干预促进产业发展、维持国家竞争力的一面。2023年4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杰克·沙利文(Jack Sullivan)在演讲中提到“新华盛顿共识”,强调美国应动用国家力量复兴美国产业、巩固科技优势,从而维持领先地位。自此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美国政府作为“发展型国家”的一面。
特朗普上任之后,维持了拜登任内通过国家干预巩固前沿产业优势的大方向。只不过,在产业支持方法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与拜登政府迥异的做法。特朗普叫停或削减了拜登任内出台的可能带来大量财政支出的部分产业补贴政策,尤其是暂停了对新一代能源产业的支持和气候外交。相比之下,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大力倚重硅谷科技右翼构建新型“发展型国家”。本报告的目的就是对这一方面进行梳理与分析。
渊源:特朗普政府为何大力启用硅谷科技右翼?
特朗普对于硅谷科技右翼的倚重,与后者在价值观上奉行“科技服务国家利益”的原则直接相关。
与传统的技术官僚有所不同,科技精英标志性的特征是他们对于科技如何复兴美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思考。这些思考在他们所出版的著作中都有所阐述。例如,在《电线之战:技术与全球权力斗争》(赫尔伯格著)中,作者用“灰色战争”(Grey War)来命名当代冲突,强调对抗常态存在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并且天然具有双用途属性,民用平台和基础设施既能服务商业,也能被国家行为体改造成影响力投送与控制工具。在《科技共和国》(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著)中,作者反思美国科技雄心的丧失及其原因,认为美国应当依托科技优势重新建构霸权、拯救国家。作者认为绝对的技术优势使美国形成足够的威慑能力,从而带来和平,而人工智能行业是美国奠定技术优势地位的重点依托。书中提到,“为了让美国及其盟友保持其全球优势——并维护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软件行业必须重新致力于解决我们最紧迫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的新军备竞赛。政府必须大力借鉴奠定硅谷成功基础的工程思维”。作者提出“硬实力”与“软信仰”概念,即技术与价值观的统一。所以说,硅谷科技右翼“科技服务国家”的主张与国家目标有高度的契合度。
图左为《电线之战:技术与全球权力斗争》(赫尔伯格著),右为《科技共和国》(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著)(图源:作者整理自网络)
其次,在思想和行为特征方面,硅谷科技精英具有明显的“工程师思维”,高度遵循理性主义和效率优先原则。理性主义被运用到方方面面。例如,“有效利他主义运动”旨在通过计算每笔捐赠将有多少人受益来重塑慈善事业,这本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模式。这种行为特征与企业家出身的特朗普的工作风格非常相符。
再者,科技精英的背景与特朗普本人摆脱建制派官僚,即“深层国家”的意图相一致。特朗普与“深层国家”的嫌隙已久,后者被认为是使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之内政策施行遭遇阻滞的关键因素。因此,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特朗普大量任用亲信进入内阁,形成思想统一的核心班底。硅谷科技右翼对于所谓的“民主”不乏批判。他们认为“民主”已经吞噬了美国的国家能力,是造成美国现今实力减退的重要原因。大力启用理性主义、不讲求民主教条的科技精英是特朗普推行其政策的有力一环。
科技右翼在美国新型“发展型国家”中扮演的角色
在开启第二任期的一年以来,科技右翼已经广泛渗透到特朗普政府的各项工作中,重点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作为核心幕僚制定关键产业政策。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任命多名硅谷科技精英进入其核心幕僚团队。其中包括现任总统科技事务助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J. Kratsios)、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特别顾问戴维·萨克斯(David O. Sacks)、白宫人工智能高级政策顾问斯里拉姆·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总统科技顾问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等。他们都有在硅谷的长期工作经历,并且大部分与硅谷科技右翼灵魂人物彼得·蒂尔(Peter Thiel)有共事经历或私交甚好。作为白宫的核心幕僚,他们主导了特朗普政府AI相关产业政策制定和关键议程的推进。其中,克拉齐奥斯和萨克斯是2025年7月颁布的《美国AI行动计划》的署名者。克里希南虽未署名,但也是共同撰写者。他们被认为促成了“星际之门”计划,并作为科技政策代表团的成员,在美国针对中东的“人工智能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
图左为现任总统科技事务助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Michael J. Kratsios),图右为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特别顾问戴维·萨克斯(David O. Sacks)(图源:作者整理自网络)
第二,进入内阁或在各内阁牵头的政策制定中发挥咨询职能。除了担任核心幕僚以外,部分硅谷科技精英进入内阁,成为核心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中,去年十月履新的国务院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事务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就是代表。赫尔伯格有过在谷歌等科技公司的任职经历。自2023年起,他担任国防科技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首席执行官高级顾问。在组织动员层面,他参与推动连接国会山和硅谷的“山谷论坛(Hilland Valley Forum)”等跨界平台,将科技企业、风投与国会议程放到同一张桌子上讨论,形成聚焦中美科技竞争的持续对话与动员机制。出任副国务卿以来,赫尔伯格主导了“硅治下的和平(PaxSilica)”计划,在科技外交方面非常积极。科技右翼参政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是伊隆·马斯克(Elon Musk)。他曾经领衔“政府效率部”,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硅谷科技右翼在内阁所牵头的政策制定中发挥咨询职能。在《AI行动计划》中,明确要求商务部等内阁在制定政策时,需听取总统科技事务办公室和总统科技顾问的意见。
国务院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事务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图源:作者整理自网络)
第三,主导与业界相联系的标准制定。2025年6月,商务部正式宣布将下属于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AI安全研究所(AI Safety Institute,聚焦AI风险与安全)更名为美国AI标准与创新中心(Center for AI Standards and Innovation,CAISI),并调整重点为推动AI标准、测试、合作与创新等工作。这个中心由保罗·克里斯蒂亚诺(Paul Christiano)负责。克里斯蒂亚诺曾经在OpenAI工作,是业内享有盛名的科学家。他在业界的广泛人脉为CAISI牵头制定符合业界需要的标准、和公私部门合作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在《AI行动计划》中,明确建议CAISI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邀请联邦机构和研究界人士参加,分享构建人工智能评估方面的经验和最佳实践。
第四,参与国家核心安全议程。硅谷科技右翼已经成为“技术-安全复合体”的重要部分,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借助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防务创新小组、山谷论坛等机制,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与科技界不断深化沟通协调,后者也试图借此为自身谋取更大利益。其中,帕兰蒂尔公司(Palantir)、安杜里尔公司(Anduril)、太空探索公司(SpaceX)与美国防务部门有着多年的合作经历。
如何评价特朗普政府构建的新型“发展型国家”?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对“发展型国家”的构造并非特朗普政府的专属。从奥巴马时期到拜登时期,美国逐渐加速推进这一议程。在拜登时期,美国对发展型国家的构建基本完成了对内、对外两部分政策框架。对内,拜登政府先后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贸易扶持及一系列人才政策,全面强化美国在半导体和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本土制造能力。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领衔推动新兴技术的研发和标准制定,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负责实施技术出口管制。财政部为美国产业补贴进行拨款,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实施金融制裁。财政部领导的跨部门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对与国际利益密切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对外,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产业联盟。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提倡“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激励制造业回到美国近土或盟伴国家。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这些旧有工具的基础上,通过对科技右翼的大胆任用,为美国的“国家能力”赋予了一系列新特征,并预期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看,科技右翼所主导的AI产业战略正在引领新一波产业繁荣。特朗普政府对于国家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认识与拜登政府有所不同。在“国家应当在什么环节给予支持”这一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反对产业补贴,而是强调去监管、基础设施建设、联邦层面的数据共享、行业标准制定、政府需求创造以及与业界沟通渠道的建立,确保产业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需求相一致。在资金方面,强调不占用政府财政资源,而是依靠已有的风险投资体系来促进技术创新和行业发展。
科技右翼的参与正在将发展型国家的“嵌入性”一面发挥到极致。硅谷科技精英出身于业界,因此对于科技与产业结合高度重视。在政策制定层面,他们高度发挥“旋转门”功能,将硅谷科技企业的诉求传达到白宫,运用“山谷论坛”等平台将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国家安全相结合。总体来看,在科技右翼所主导的AI产业战略下,美国在AI领域正在兴起新一波产业繁荣。
从消极的方面看,科技精英的主导权可能缺乏制约,长远来看可能使美国模糊优先议程,丧失国家“自主性”。并且,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有将美国带入战争的危险。
美国的目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尖端技术优势来调动资源完成自身经济的“再平衡”,其中的关键是让盟友承担美国经济“再平衡”的成本。因此,在对内政策方面,美国通过“去监管”、联邦层面推进基础设施、数据共享等方式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对外政策方面,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以允诺高端芯片出口、关税豁免、将对方纳入以美国为主导承载“民主”价值观的前沿科技体系为条件,要求对方国家对美国加大投资,帮助实现美国依托前沿产业“再工业化”,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按照罗德里克的“三元悖论”(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民主制度不可兼得),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以牺牲民主和对权力的制衡为代价。拜登在2025年1月15日的告别演讲中发出警示,指出一个“科技-工业复合体”正在兴起,技术、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对美国经济“再平衡”的贡献很难说。《华盛顿邮报》近期报道指出,自从特朗普在2025年4月声称他的大规模关税政策将开始让制造业回归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每月连续下滑。目前美国的工厂雇用约1270万人,较特朗普去年4月宣布关税政策时还少7.2万人。其中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约有一半进口品属“中间环节”商品,即美国企业用来制造最终产品的原料。进口品征税对中小型企业打击更大,因为关税对生产用商品价格的推升幅度,远高于一般消费品。因此,对科技右翼的大力启用是否会危害美国国家的“自主性”,扭曲核心议程,有待持续观察。
对我国的启示
特朗普政府通过大力启用科技右翼打造“发展型国家”的实践可给我国诸多启示。此举本质上是通过总统授权,将核心政策交给价值观一致的科技精英拟定,并通过总统的行政令调动内阁部门执行。这种做法在决策、资源调动上效率非常高,符合前沿科技创新活动的需要。这一点值得我国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加以借鉴。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到美国大力“押注”AI等前沿科技,其实质是巩固霸主地位。AI等前沿技术优势的获得可以显著提升美国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筹码,为本国的内部“再平衡”赢得空间。但这种手段是否实现制造业的回流以及美国经济的“再平衡”还有待观察。
中国当前的优先议程是主权、发展与安全,而非与美国争霸,因此不必要陷入与美国在科技竞争方面“零和博弈”的叙事。历史上的技术革命都要求技术广泛嵌入于经济活动和社会需求。中国在芯片行业的发展路径证明了,繁荣的产业生态是创新和技术迭代的关键。我国有大量的产业应用场景,并可以通过在质量和价格上有竞争力的技术拓展东南亚等外部市场。将AI与产业相结合,将是中国利用这一波技术浪潮实现发展的重要路径。
中国和美国在前沿科技领域还有差距,这是事实。中国不需要排斥美国的AI技术体系,也不必要在当下就倾注大量资源建立排除美国在外的技术体系。技术的发展靠的是制度的开放、人才的汇集和思想的交流。在美国处于大方向上“收缩”的趋势时,我们要逆流而动,坚持开放战略,走好自己的路。
*本文选自《APEC与主要经济体改革动态分析》2026年第1期。
GBA Review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