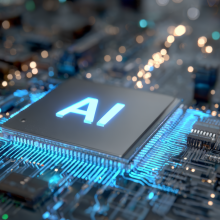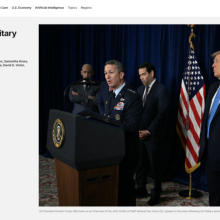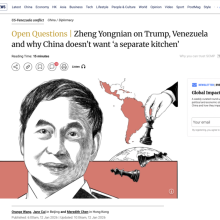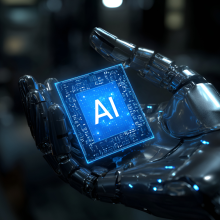编者按:传统视角总是将“全球南方”看作是“不确定”的异常,然而现实中更多情况下“不确定”才是常态。本文借鉴葛兰西对意大利南方的分析,强调了理解“全球南方”的关键不在于分析其原因,而在于探讨塑造其困境的全球结构性不平等的底层逻辑。美国作为曾经的发展范本,如今地位已岌岌可危,而中国的“双循环”战略以庞大内需为杠杆,撬动了“全球南方”全方位依附于北方国家的现状,为打破市场端的垄断提供了可能——这不仅是对全球市场的重塑,更是一场追求实质平等的远征。
一、“全球南方”问题体现出的理论贫困
当今围绕“全球南方”而展开的讨论,研究者们最常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全球南方”。在传统的定义中,“全球南方”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模糊的、不具有任何学术内涵的概念。过去一年西方学界对“全球南方”的定义,或者在强调它的不确定性,或者将其等同于某种政治联盟与地缘政治范畴。
如何理解不确定性?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对“全球南方”理论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因为在既有的认知里,我们会追寻某种确定性,这是对世界秩序最根本的诉求。但是不管是在实践还是理论中,我们都面临大量的不确定性。过去的理论研究把这种不确定性当作是例外甚至非正常状态。这种不确定性的产生,其实是源于认识论层面上对确定性的理解局限。
如何理解确定性?西方现代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秩序观。所有关于既有的国际秩序的描述,都是围绕着某种秩序性和确定性展开的。这种确定性来自于权力以及资源等各方面自上而下的垄断。在这种垄断之下想象出来的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在我们看来就是稳定的。而实际上,所谓的稳定性并不是真的长期存在。一方面我们有对于稳定的诉求,但另一方面我们面对更多的是对这种稳定性的冲击。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作为被统治、被管理对象的“全球南方”自然会显得杂乱无章。我们今天在理解“全球南方”的时候,也经常会从这种认识论出发,想当然地把“全球南方”描述成不统一、不确定、不稳定的对象。这很大程度上也显现出了既有西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知识体系 “理论贫困”的结果。
葛兰西对作为地理概念的 “南方”有过一个极具辩证法意味的讨论。他在讨论意大利统一所面临的障碍时,注意到了意大利南北之间由于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形成的发展差异。并且,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差异被叠加上了意识形态意味之后,造成了意大利北方对南方的文化歧视。意大利的南方以农业的生产结构为基础,同时面临着北方的工业生产结构的挑战。对于葛兰西而言,讨论南方问题的根本在于他希望在“统一的意大利”的目的下,思考如何让南北发展高度不平等、经济基础高度不一致、文化习俗高度差异化的意大利能够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且继续发展。
在葛兰西看来,南方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地理范畴,但“南方问题”的形成,则是在人的活动基础上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南方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构成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秩序。然而,在工业化的北方看来,南方却成为了文化上落后的、野蛮的、保守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是发达的、先进的、现代的北方。恰是这种描述蕴涵了一种深刻的决定论理论,它强调南方的不发达是与其本质密切相关的,并非是出于某种结构性的原因。葛兰西认为,在处理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的问题时,必须要将南北方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放在统一的框架内理解。
同样,我们今天在理解“全球南方”的时候,问题并不是“全球南方为何不发达”,我们应当问“在怎样的结构当中创造出了‘全球南方’的问题本身”。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我提出今天对于世界秩序,包括发展秩序在内的理论本身,需要回答的三个根本的认识论的问题:第一,我们为了谁发展?第二,我们向着什么去发展?第三,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发展?
二、“美国优先”——历史参照系的消失
过去,从冷战末期到21世纪初这30余年中,为了谁发展、在什么条件下发展,以及发展后会怎样的问题是不需要回答的,因为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人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就是变得更像美国。美国冷战后的胜利主义建立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美国全球军事霸权形成的基础上。对世界其它国家而言,美国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模仿的对象、唯一一个可供参考的中心。所有的知识体系是围绕着如何变得更像美国而建造起来的。但是在过去的10年当中,这个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前面跑的美国“不在”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具有乌托邦意味的问题,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想自己如何以及朝哪个方向发展,就变成了一个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美国作为唯一中心的衰退是这些年中最为世人瞩目的事件。随着美国中心地位的衰弱,中国以及整个“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进程也是这一历史时期中极为重要的事件。两者之间并非简单地互为因果。从辩证法的视角来看,美国中心地位的衰落,是霸权秩序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发展结果。而中国的崛起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非中心国家实现去依附发展的现实案例。
去依附发展在现阶段引起的最直接反应,就是中心国家在维持霸权结构的目的驱动下,对世界发起的贸易战、关税战。中国则在这场斗争中,成为了去依附发展模式的重要堡垒。而去依附的现代化发展则是“全球南方”,乃至整个世界所应当共同追求的未来。
如何理解贸易战?我觉得讨论国际秩序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就是我们默认国际秩序的稳定性来自于美国这个统一的权力来源。但是很少有人进一步在历史以及辩证关系当中,理解美国的垄断到底存在于哪几个方面。过去我们经常围绕着单一的生产环节讨论垄断。的确,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打破在生产端的垄断,我们通过变成全球工厂摆脱了原先的被压迫地位,但这仅仅回答了过去改革开放30年中的问题。依附理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国际公司已经开始将生产端转移到“全球南方”。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条的形成,生产端的垄断已经被打破。然而,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随着生产端向“全球南方”转移,“全球南方”仍旧是依附性的、无法实现自主发展的?无法将生产端产生的部分剩余价值投入到本国经济循环以及再生产中,实现真正的面向健康增长的积累?这与仍旧普遍存在的市场端、需求端的全球依附结构密切相关。
今年特朗普发起关税战所围绕的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为什么大家要“跪”?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恰恰是由于对这个最大的统一市场的需求,导致所有国家不得不将它的产品卖给美国——这就是特朗普搞贸易战最根本的逻辑。“全球南方”在发展进程中也清楚意识到了,其对于北方的依附不单纯是生产知识上的,而是全方位的。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南方”寻找市场、希望建立起良好循环的时候,发现除了北方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卖”。
这并不是上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问题。英国在19世纪就建立起了全球循环体系。举例来说,例如加纳——也就是独立之前在欧洲殖民者眼中的“黄金海岸”——它经济的绝对支柱是可可豆出口。而可可豆的最大消费市场恰恰就是他们的旧殖民主——欧洲。殖民者为了资源与可可豆,将加纳编制到自身的殖民经济全球循环中,建立起了从生产端到需求端的完整链条。这一循环链条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将“黄金海岸”原有的经济自主循环彻底破坏,并将其转化成为具有高度依附性的、无法自给自足的、以欧洲市场需求为锚的殖民全球化循环中的齿轮。从上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开始,“全球南方”的诉求就是希望从多方面摆脱这种依附性,其中包括对生产能力垄断的摆脱,以及对于“全球南方”内循环的诉求。但出于很多机制性的原因与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这个循环始终都没有建成。在“全球南方”谋求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中,不缺乏失败的经验。将中国实现去依附现代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与“全球南方”绝大多数国家无法实现去依附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相比对,我们就不难发现,“全球南方”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去依附发展的重要掣肘之一就是无法掌控本国货币的主权。在国内生产循环中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无法以资本的形式投入到再生产当中,也就是说,通过生产产品所积累的价值无法进入本国再生产的循环。“全球南方”经济文化与政治精英们通过加入“全球北方”生产全球化链条而获取的利润,绝大多数重新流入到了“全球北方”,成为伦敦纽约等核心城市的昂贵房产、奢侈品、教育与服务市场的消费力量。这种无积累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制约了过去“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发展,也造成了“全球南方”国家经济高度买办化的基本现状。
三、中国方案的理论与实践
在这个背景下,理解中国自贸易战以来,特别是今年年初以来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设想,会发现中国不再仅局限于自身作为世界大工厂的意义,而且多次提及“双循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中国可以为原本高度依附于“全球北方”消费能力的全球市场提供一个多样的需求端。简单来说,中国在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几十年中,不仅要向全球卖,更多的是向“全球南方”国家宣称我们可以买,我们可以变成“全球南方”依赖的更大的共同市场之一。这是今天提及双循环的意义,也将为我们讨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抓手。
回到中国传统的发展观当中。张培刚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指出,如何在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家共同体里实现现代化。把视角变换一下,这同样也是中国以及整个“全球南方”要回答的发展问题——如何在一个发展阶段高度不平衡、不平均的状况下实现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最给“全球南方”国家启迪的中国经验,恰恰是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齐头并进,以及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先锋党,通过国家力量推动形成更大共同体,并且通过保护性关税以及主权货币工具,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并确保这种积累能够进入到共同体经济再生产循环中。
当知识界回望上世纪80年代,仿佛觉得中国已经开始全面模仿美国的时候,中国的思想家们仍具有极强的中国主体性意识。这恰与“全球南方”产生了最深层次的知识共鸣。在这里我想援引复旦陈其人先生的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指出历史辩证法最终将会消除南北经济差异。今天中国讨论“全球南方”,并不是在说“全球南方”的本质属性到底是什么、由哪些国家或地区组成、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作“南方”,而是指出“全球南方”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严重的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并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在承认了既有全球化进程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探讨如何通过自主发展来推动不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现代化,并且消解全球化发展高度不平等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性的表态,就在于我们不仅仅强调要寻求形式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希望探索实质上的平等。这与强国家建设密切相关。不能简单地复制原有的或者是西方中心的国家理论,更多的是要在国际互助、强国家建设的条件下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性的发展,这也就回答了为了谁发展的问题。
GBA Review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