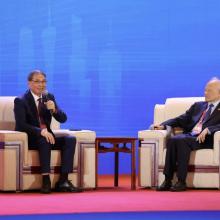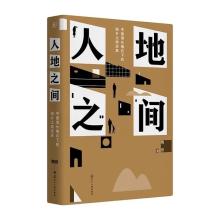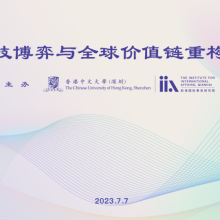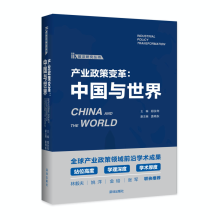編者按: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基本保持着和平稳定。然而近日,南海波澜再起。菲律宾频繁拉拢域外势力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11月14日至15日,菲律宾武装部队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及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所谓“西菲律宾海”再次开展多边海上合作活动(MMCA),“彰显了地区团结与合作日益加强”。
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报告《修辞与现实:菲律宾、东盟和南海》。本文从海外视角进行深度分析,直指美国南海政策的核心逻辑:并非真心维护地区稳定,而是将南海视为遏制中国崛起、维系自身霸权的关键棋盘。文章指出,菲律宾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外交政策路径:在原则上重申东盟中心性的同时加强美菲合作,同时拓展其他战略伙伴以寻求在地区对抗大国影响力。
究竟谁是南海和平的守护者,谁是麻烦的制造者?读完此文,答案不言自明。2025年8月21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面向全球发布“南海真相”系列中英文智库报告。报告系统性阐明了中国对南海诸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揭露了域外势力插手“南海问题”的事实真相。中方立场一贯清晰而坚定:我们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愿与地区国家共护南海和平。
*本文原载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原题为Rhetoric vs. Reality: The Philippines,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随着东盟峰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落下帷幕,菲律宾正为于2026年接任轮值主席国一职做准备。此次担任东盟主席恰逢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不仅是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的十周年,也处于中菲在南海关系日益紧张的敏感时期。菲律宾总统费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小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多次表示,推动早已陷入停滞的“南海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 CoC)谈判达成共识,将是其担任主席期间的优先事项。然而,从实际行动来看,马尼拉对CoC的强调更多流于象征性,其在应对当前安全挑战方面的实质性进展,恐怕将更依赖于其不断扩展的防务伙伴网络,尤其是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而非寄希望于东盟的集体共识。
今年的东盟峰会凸显了该机制在应对南海问题上的结构性局限。大多数ASEAN成员国在会议中发表的声明依旧谨慎,普遍回避对近期事态发展的明确表态——包括中国宣布在黄岩岛设立自然保护区、部署浮标、以及持续对菲律宾船只进行撞击和水炮驱离等行为。作为2025年东盟主席国,马来西亚总理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重申,应通过东盟框架内解决争端,并警告称“外部势力”的介入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尽管马科斯在公开场合认同这一立场,其政府却依然积极寻求东盟以外的安全合作关系,以遏制中国在海上进一步的行为。
与易卜拉欣较为克制的语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科斯的言论被菲媒形容为“强硬”。虽然并未直接点名中国,他仍然对所谓“不安全的操作行为以及对菲律宾在海域和空域内进行正当、例行活动的干扰与阻挠所使用的胁迫性工具与装备”表示批评。在第20届东亚峰会上,马科斯的表态更为尖锐。他谴责中国在黄岩岛设立自然保护区的举措,并称该地“长期以来是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马科斯表示,其言辞并非挑衅,而是反映了菲律宾在南海所面临现实情况的“必要表达”。他还补充道,如果东盟“无法解决问题,至少我们应当持续寻求某种方式来管控紧张局势……为各方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处机制(modus vivendi)”。
美菲“呼朋唤友”,影响南海局势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言论反映出菲律宾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外交政策路径:在原则上重申东盟中心性的同时,持续拓展与其他战略伙伴的合作。尽管菲律宾仍然支持“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程,但谈判进展缓慢,这进一步加深了其国内的共识,即仅凭东盟机制难以在南海实现实质性的安全成果,尤其是在当前紧张局势已对菲律宾公民的安全与生计构成直接威胁的背景下。
在东盟防长扩大会(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上取得的进展,揭示了菲律宾当前安全政策的实质性突破所在——这些进展发生在东盟峰会闭幕后近一周的时间里。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克塞思(Pete Hegseth)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特·特奥多罗(Gilberto Teodoro)联合宣布成立“菲律宾特遣队”(Task Force Philippines),并完成了《联盟战备行动计划》(Alliance Readiness Action Plan)。该特遣队参考了2024年公布的“阿云金礁特遣队”(Task Force Ayungin,阿云金礁即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设立模式,后者是一个专注于应对南海潜在危机的美军单位,旨在进一步深化当前由美菲联合军事援助小组(Joint U.S. Military Assistance Group)协调的相关合作。新成立的“菲律宾特遣队”将隶属于美国印太司令部,任务范围预计将比其前身更为广泛,涵盖包括灾害救援在内的多项任务,尤其是在菲律宾群岛范围内的应急响应能力;尽管如此,南海仍将是其重点关注区域。该特遣队预计将编制约60名常驻人员,由一位准将或同等级别的海军将领领导,从而提升对突发情况的快速应对能力与战略灵活性。
特奥多罗部长强调,美菲之间不仅要加强双边联盟,还必须“吸纳更多盟友”——这一目标菲律宾已在积极推进。上周末,菲律宾与加拿大签署了《访问部队地位协定》(SOVFA),这是渥太华在印太地区签署的首个此类协议。此外,在2025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场边会见中称菲律宾为“特殊朋友”,呼吁两国加强合作;与此同时,韩国韩华海洋公司(Hanwha Ocean)也承诺将支持菲律宾海军正在筹建的潜艇项目。
上述进展进一步丰富了菲律宾近年来不断扩展的防务合作网络。除与日本达成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外,菲律宾还与新西兰签署了SOVFA,与德国缔结防务合作协议,并与印度建立了多项防务合作安排。此外,菲律宾与法国也正在就自身版本的访问部队协议进行磋商。这些防务协议凸显出菲律宾正在积极构建一个超越东盟框架、具备威慑与能力建设功能的多边安全伙伴网络。
展望未来,菲律宾面临一场敏感的战略平衡考验。作为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将有机会重申东盟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核心作用;然而,这一角色也要求其在东盟内部存在明显分歧的背景下,谨慎处理部分成员国试图回避与中国直接对抗的立场。马科斯当前所采取的路径展现出一定的务实态度。菲律宾很可能会利用其主席国地位,继续强调“南海行为准则”机制对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藉此表明东盟对和平秩序的承诺,即便对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并不抱过高期待。与此同时,马尼拉也将持续深化其“次区域小多边”(minilateral)防务合作网络,以实现东盟共识机制所难以达成的实际安全成效。
If successful, the Philippines could position itself as both a defender of ASEAN centrality and a driver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the success of which will shape not only Manila’s chairmanship but also Southeast Asia’s trajectory in navigat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
菲律宾即将担任的2026年东盟主席国角色,既具象征意义,也具有战略价值。一方面,该年份标志着菲律宾在海牙国际仲裁中“胜诉”十周年(译者注:2016年,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作出最终“裁决”,荷兰海牙法庭判菲律宾“胜诉”声称,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并否定了中国主张的“九段线”),凸显其对以规则为基础的海洋秩序的长期承诺;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契机,使菲律宾政府得以在南海问题上协调东盟外交路径与现实安全需求之间的张力。马科斯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坚守东盟原则的同时,有效推进本国国家利益。如果运作得当,菲律宾不仅可塑造成东盟中心性原则的坚定维护者,也可能成为推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的关键力量。这一角色的成功与否,将不只决定菲律宾主席国任期的表现,更可能影响整个东南亚在应对海上大国竞争中的战略走向。
本文作者
Monica Sato: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海事透明倡议(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研究助理。
本文译者
周宇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IIA学术编译组成员。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IIA学术编译组成员。
*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大湾区评论或IIA机构立场。
*编译原创声明:本文编译版权归微信订阅号“大湾区评论”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侵权必究。公众号授权事宜请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权事宜请联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