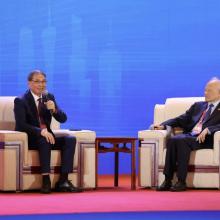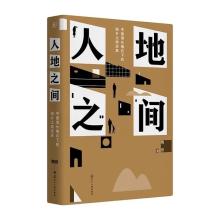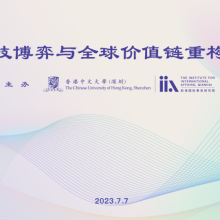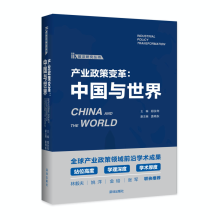編者按:当地时间10月30日,中美元首在釜山举行会晤,为持续紧绷的中美关系按下“暂停键”。这场会谈虽未解决根本性分歧,却在硝烟暂歇时打开了一扇对话的窗口,也让世界关注:这场大国博弈将走向何方?
本文提出十个关键判断,直指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已从意识形态打压转向对切实利益的交易,未来中美关系的核心很可能不再是“谁战胜谁”,而是双方如何在竞争中长期共存。
作者敏锐指出,美方的战略收缩与中国的持续发展形成结构性互补,而台湾问题等敏感议题可能被特朗普视为可交易的筹码——这种冷酷的务实主义,反而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创造了可能性。“中美都需要学习与竞争对手维持‘长和平’相处。”文中这句话道破了当今国际关系的本质。当特朗普将“G2”重新摆上谈判桌,我们是否已准备好超越“霸权分赃”的旧思维,构建真正平等的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在这场持久博弈中“竞争性共存”,这一问题值得每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深思。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釜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并且会晤前后,特朗普都高调地在社交媒体上以“G2”这样的渲染词语对中国给予了礼遇和基于国家实力的承认,中美关系似乎暂时“停火”,忧中见喜。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针对“特朗普2.0”以来,特别是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和走向趋势,我们初步形成了十个判断。
(一)本次元首外交信号:中美关系“脆弱缓和”但前景可期
本轮中美元首见面,西方少数观察家的评价形容是“脆弱的缓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研究员大卫·萨克斯指出,中美双方“达成了临时休战,但未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的任何根本问题”,许多结构性矛盾仍悬而未决。美国之音等媒体评论称,会晤成果更多是象征性的“止血”,真正的贸易战停火仍然脆弱。如果单纯从本轮会面的成果来看,本次会面只能说是前期中美经贸关税争端的一次中途“停火”,但从中美关系的长期博弈态势来看,我们认为本次会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功:
1. 中美双方对“胜负”的共识
一是中美双方、特别是美方对华鹰派和中方反美人士都基于现实认识到,中美关系没有“胜负”,中国与美国将基于国家实力重新界定双方的权力边界,重新校正彼此的关系定位。中美双方都要适应两国的竞争性共存状态。
2. 国家利益的协调方式
二是中美之间不是只有对抗,谈判与交易也具有重要价值,中美双方都应该高度重视元首外交的作用。长期以来,中美谈判交易存在结构性错配:美方强调自上而下由领袖“拍板”决定,特朗普希望多次表达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的尊敬,希望可以直接会谈,再交由行政层去执行;中方则希望先由行政层面确立初步框架协议,再推动元首会晤。于是双方谈判进程较为漫长曲折,出现的摩擦主要源于中美决策结构差异所导致的战略性误会。本轮通过元首外交的直接面谈,为中美关系的后续缓和开了个好头,也为我们今后推动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即充分理解和对齐中美两国在决策和谈判结构层面的差异。本次会议,让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国家利益的协调不应局限于所谓的民族情绪,而是应当通过理性谈判和务实交易的方式加以解决。
在前往韩国釜山参加峰会前,特朗普在他的账号上发文(图源:推特截图)
(二)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支线,并非政策决策层的主要关切
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的重要特点是“外交服务内政”,即对外关系服务于国内事务。其中,中美关系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部分,但并非主线关系。特朗普所实施的一系列看似“荒诞反复”的内外政策,并非是意识形态偏见或是个人单方面冲动,而是旨在解决美国国内长久以来真实存在的问题积弊。当前美国的对外政策正是特朗普为解决国内五大核心问题所做的考量——政府赤字与债务、全球治理负担(霸权成本过高)、自由民主道义包袱(非法移民问题)、产业空心化与深层政府问题。特朗普正处在推动国内深层改革的关键阶段,将面临来自美国内部的多方力量掣肘,因此其主要精力将聚焦国内事务,并且其政策核心指向并非是要全方位针对和遏制中国。
此外,在对外关系中,特朗普对欧洲、加拿大、墨西哥,拉美、日韩与东南亚国家等均采取了一系列从经贸到安全领域的一系列动作,但是中美对抗的叙事仍然更为吸人眼球,导致中美关系在舆论上被放大为美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关系。我们认为,中美关系只是占据的经济利益比重较大,但是与美国其它对外关系相比并无特殊之处,美国也不会专门针对中国采取特殊性政策。
(三)中美关系的底层逻辑:是特朗普对中国的需要,而非对中国的遏制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认为美国的问题是中国造成的,因此以反华为其主要主张。特朗普在竞选前是政治素人,其对中国的判断与态度一是来自于与中国做生意的经历、二是来自于周边朋友与幕僚。其第一任期缺乏国家治理经验,加上周围幕僚蓬佩奥(Mike Pompeo)、博尔顿(John Bolton)、班农(Steve Bannon)、博明(Matthew Pottinger)、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等人对华基于意识形态的无条件地打压和遏制,促使特朗普将打击中国作为第一任期的主要政策主张。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已认识到美国的问题是美国自身的,其要做的就是推进国内的深层次改革,而不是将罪责推卸给中国,但是特朗普希望中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解决美国内部的经济与财政问题。因此,其政府班底也出现明显调整:第一任期内主张无条件遏华反华的人士都被清理出局,取而代之的是少壮派的对华事务官员,该团体更加客观,对特朗普本人的意志更加忠诚。即使是共和党内长期反华的国务卿鲁比奥,也放弃了其一贯的反华形象,转而服从特朗普的整体对华态度。特朗普目前就是认为中国前期从美国赚取了过多利润,希望中国在今后的贸易谈判中予以让步,缓解美国的贸易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特朗普需要的是中国的帮助,而非以对抗遏制中国为目的。
(四)中美关系可绕开“修昔底德”陷阱而避免对抗
“事不关美、高高挂起”,中美之间不存在无条件的冲突。从特朗普及“MEGA”派的美国优先、特别是美国国家利益为主的政治主张看,相较于传统建制派美国总统以及意识形态反华精英,特朗普及其幕僚团队对中国政策态度总体保持了相对客观:当中国侵犯了美国国家利益时,其便与中国展开斗争;当中国事务与美国国家利益并不相干时,也不再针对打击中国。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中美关系将来潜在的冲突一定是中美两国现实中的利益矛盾,特别是经贸、货币以及民生领域的矛盾,但是不太可能产生无条件的对抗遏制,两国的谈判与斗争都将是常态,而不会演化升级为国家间的对抗。
(五)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必然性
中美战略利益的结构性互补创造了“交易空间”,决定了中美关系必然可以坐下谈判达到缓和与合作。
特朗普的利益诉求与中国的利益诉求本质上具有互补性而非互斥性,两国走向合作是必然。特朗普强调扭转贸易赤字、减税降息、裁减政府、产业振兴等一系列政策,都凸显特朗普亟需解决美国国内实际存在的问题,其更加倾向于经济利益目标的实现,对所谓的意识形态对抗、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捍卫等并不在意。
至于我方,在产业技术升级、全球力量与资源布局、台湾主权归属问题认定、国际承认与责任担当方面、制度优越性和政权合法性方面都对美国方面的承认和支持具有较大的需求。而我方在国家产业规划与动员能力、超大规模市场、劳动力人口基础、经济产业比较优势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和让步空间。中美双方的国家利益存在客观互补空间,这就为中美达成最终交易提供了可能。
(六)美国对外姿态呈现战略收缩为我方经略东亚和全球创造空间
美国的国家战略姿态逐步表现为“战略性回缩”和“低成本霸权”,国家战略重心逐步转向对美洲大陆及太平洋的绝对控制能力,而非以往所推崇的欧洲与东亚的“双线平衡战略”。一是从全球战略力量部署重心看,美国实施了战略性回撤。特朗普最近在北美与周边地区的系列举措,包括对加拿大、格陵兰岛的领土诉求、对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的主导性调整,以及从经贸延伸到安全领域实施对拉美国家的拉拢、威逼、控制,都显示美国的战略重心回归到了以美国本土为核心、以美洲大陆为基本盘的思路,其不会强调全球霸权的实质性存在。二是从其2025年《新国防战略》草案来看,美国实施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收缩,强调“回归本土防御”(Homeland Defense),优先西半球安全,避免资源过度投入与中国印太对抗。这与特朗普“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和“实力求和”(Peace Through Strength)议程高度契合,实质上从“印太重心”转向“本土为本”。三是从美国介入全球冲突的方式看,其更加青睐于斡旋、调停、武器静默等“低成本霸权”模式,不愿意直接军事介入。因此,美国也绝不会实施与中国的军事对抗,也不会因为台湾等第三方因素与中国军事对抗,转而寻求积极的谈判交易来实现。
(七)我方对美姿态:应抛弃“输赢观”、不存在战略反攻、要与美长期和平下“竞争性共存”
中美两国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既自主发展又相互依赖的世界性强国,一方从外部击败对方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大国对抗只能陷入“两败俱伤”的双输局面。美国兰德公司10月14日《稳定美中竞争》(Stabilizing the U.S.-China Rivalry)的报告显示,美国战略界的多数研究机构普遍承认,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体系性竞争对手,但并非可以被根本削弱或排除的对象。美国无法改变中国已深度嵌入全球体系的事实。于是,新的政策逻辑转向共处但防主导:既不承认平权,也不寻求彻底压制,而是在规则、联盟和话语上维持对中国的“制度性制衡”。这种思路意味着美国不再追求单极主导,而是在相互制约中维持秩序平衡。
美国对华战略态度的转变,在兰德公司发布的重量级报告中也有所体现,兰德公司战略专家也提出中美要寻求“稳定的竞争关系”或“竞争共存”而非通过“取胜”或是“一方崩溃”来定义中美关系的未来航向。
因此,我们不认同中美存在战略相持与战略反攻阶段的说法,国家的“竞争性共存”是大国关系的常态。中美关系将长期呈现竞争性共存的状态、互有来往博弈与战略牵制,而不会存在所谓的中方对美反攻制胜的问题,中国同美国一样,都需要学习维持与竞争对手的“长和平”相处。我方要扬弃“零和博弈”“你输我赢”“谁胜多输少”的对抗性思维方式,转而回归“求同存异”下利益交换的谈判合作思路,通过“帮助”特朗普解决国内内政难题换取中国国家利益难题的创新性破解。
(八)我方如何认识联盟问题:世界是否存在反华或者反美联盟?
美国难以构建国际反华联盟,但可能围绕半导体、稀土、芬太尼等建构围华制华工作机制。正是由于美国采取了国家战略收缩和“低成本霸权”的模式,美国不会再花费大成本组建类似冷战期间的“北约”组织来对抗中国。并且由于特朗普政府责任卸载和政策反复、欧盟观望情绪严重、东盟选边站队压力增大、更多国家则采取机会主义式的随机应变态度,并不会完全倒向美国。其它国家对美国更多是经济和安全上的依赖。
那么,中国是否可以构建国际反美联盟呢?我们认为,欧洲、拉美、日韩及东南亚少数国家,由于对美国安全保障上和部分经济利益上的依赖,不会倒向中国,即使不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抗,也绝对不会配合中国实施反美制美。甚至一些国家则希望中国对美“强硬”,以此换来美国特朗普对自身的团结支持,从而对冲中国的扩张。因此,中国既无理由、也暂无能力去组建国际反美联盟;既难以解决当前中美关系所亟待破解的深层次矛盾,也难以有效团结世界其他国家追随于我方,最终反将陷我方于国际孤立。
(九)特朗普为何提出“G2”概念:“霸权分赃”还是责任共担?
近期特朗普多次使用“G2”这个概念来描述中美两国的互动谈判。“G2”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现新话语表述和策略调整的重要信号,但是我们认为,特朗普重提“G2”,目前还停留在极具个人渲染色彩的话语层面,还未落实到美国对华的现实政策。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清晰度,准确区分话语层面的象征意义与政策层面的实质变化。
早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美国战略学界及政府精英抛出的“G2”概念,更加强调中国的全球大国责任,而非给予中国与美国对称的全球领导力地位,本质是要求中国在不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前提下承担更多责任,而非获得制度性话语权。准入美国主导秩序的有条件共治,并未被我国采纳。今天特朗普的“G2”概念,本质上还是“强权对话”“霸权分赃”的概念范畴,我们要谨慎对待,应当更加强调“负责任共治”“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之意。
“G2”概念,反映了美方在经过前面多轮与中方的博弈交互后,逐步开始探索明晰中美两国的边界,基于国家实力开展与中方的大国战略竞争——竞争性共存,这对当前中美关系而言是一个重大方向性转变。基于实力承认的大国竞争性合作关系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选项之一,美国决策层逐步在凝聚新的对华共识:在认识到对华遏制成本过高、与中国竞争将长期化的背景下,美国正转向探索一种设置护栏的管理型竞争模式,这种模式总体上是和平的、友好的,而非对抗的、遏制的,这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意义深远。
(十)如何理解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选择性沉默”?
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更多是将台湾地区作为一个产业回流工具及与中国交易的筹码,而非是以往美国总统捍卫民主价值制度、在亚太遏制拿捏中国的一张牌。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与中国达成一项对其有利的全面贸易协议,与中国“重新建立关系”是特朗普的“头等大事”,所有其他议题,包括台湾问题则可能先予以淡化最后再拿出来交易。当台湾议题可能干扰中美谈判大局时,美方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冷处理”,压制台湾地区的挑衅举动,避免节外生枝,这就是特朗普为何一直拒绝对台湾问题“表态”。
在与中国方面达成交易之前,特朗普政府将对台湾地区实施“产业掏空”的策略,对其形成了一套清晰的“先取后舍”战略。当特朗普逐步掏空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其下一步便是将台湾地区“卖个好价钱”,美国迫使中方在其他领域做出实质重大让步。此时,特朗普政府可能将台湾地区作为地缘政治筹码,摆上与我方的谈判桌,以在台湾地区的主权问题上做出某种姿态或承诺为交换,谋求我方在贸易顺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金融开放等领域做出实质性的、不可逆的重大让步。
*原创声明:本文版权归微信订阅号“大湾区评论”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侵权必究。公众号授权事宜请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权事宜请联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Review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