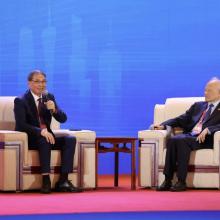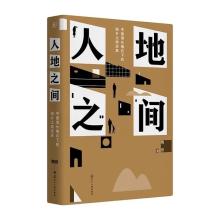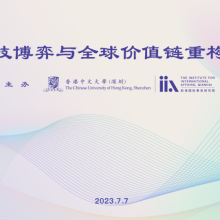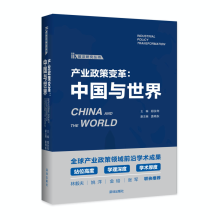編者按:思想领域的战争没有硝烟。9月7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在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上发布《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系统性揭露美国在全球开展认知战的历史和手段,深刻揭示其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严重危害。
在全球格局深刻演变、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中国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正成为关乎国家软实力与战略主动权的关键议题。郑永年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殖民”、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制度自信、南海与台湾问题的战略应对,以及中国如何吸引人才、拓展文化影响力等多重议题,提出了深入而独到的见解。
他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依赖西方理论框架解释自身实践,造成知识体系的“他者化”与“失语”。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既带来了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也加剧了西方知识体系的主导地位。他警示,在模型“喂养”的源头上,中国必须构建属于自己的内容供给,真正将几千年文明的实践智慧转化为现代知识的一部分。
讲好中国故事不能仅靠意识形态灌输或官方媒体的单一声音,而要依赖于一个“有活力的社会”,通过多样化的表达和真实的社会经验,形成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话语体系。他也呼吁学界回归理性与事实,避免“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伪学术之争。
从国家战略到个人命运,从知识体系的重建到文化软实力的拓展,再到南海问题的冷静应对与人才政策的优化,都正提醒我们,要真正走向世界,不是靠喊口号,而是靠能够被理解、被接受、甚至被采纳的思想与实践。
这是一场关于“认知”的深度对话,也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冷静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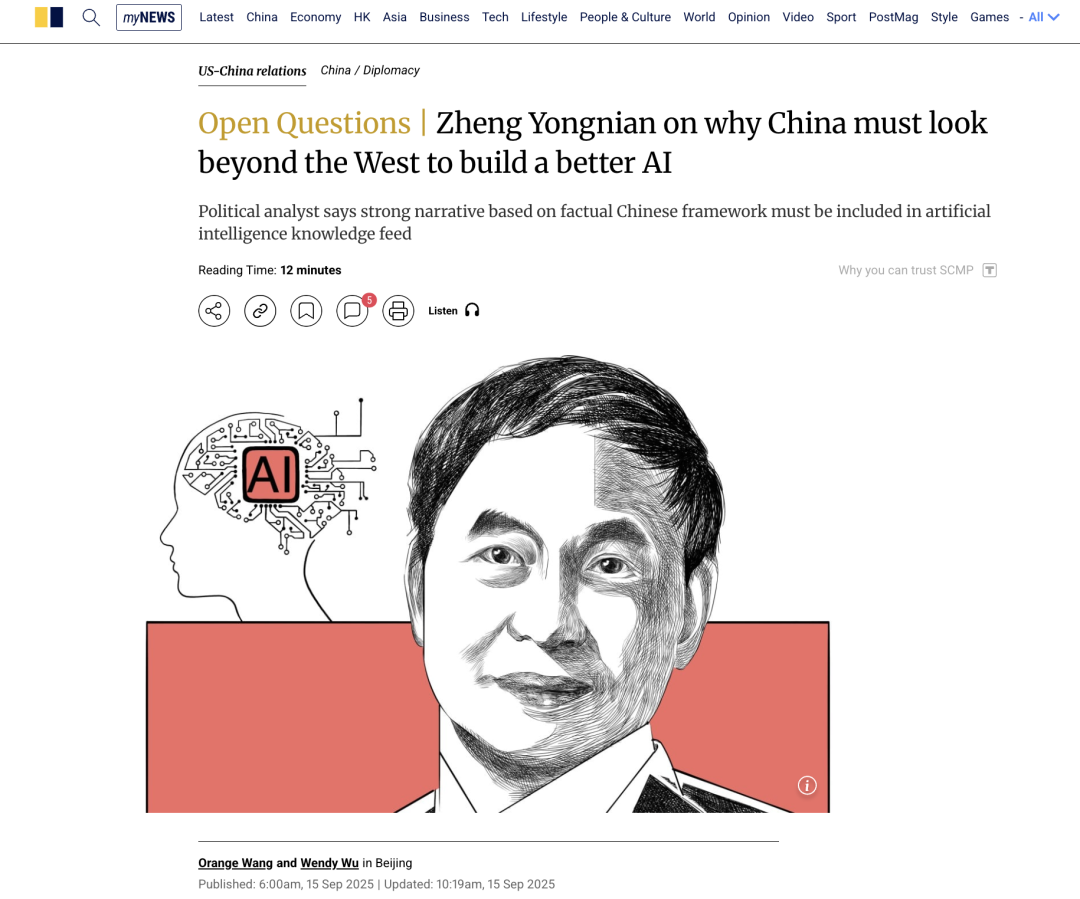
*本篇译文原载于杂志《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原题为Open Questions: Zheng Yongnian on why China must look beyond the West to build a better AI,囿于篇幅,有适当删减,供读者参考。
南华早报:多年来,您一直呼吁重建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近期,您也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殖民”表示担忧。您能具体谈谈吗?
For many years, you have called for the rebuilding of China’s own knowledge system. Recently, you have also voiced concerns about “intellectual colonialism”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Can you elaborate?
郑永年:
这些担忧主要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而这些挑战的根源来自西方。正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宗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任何国家而言都至关重要。社会与技术的意义,是由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所界定的。
中国学者学习并采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方法之上,总结的是西方的实践与经验,并用于解释西方社会。然而,这些理论未能有效解释儒家文明、伊斯兰世界和印度社会。我们应当充分接纳自身的世俗文明,从而在国际秩序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变得更加迅速。但在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的逻辑仍旧是信息的输入与提炼,本质并未发生改变。中国在DeepSeek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知识的生成方式与OpenAI的ChatGPT等模型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在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生产更趋于“趋同”而非“多元”,这使我们更容易陷入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赖之中。
南华早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学术界和战略界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时需要格外谨慎?面对构建一套符合中国自身需求的治理理念和知识体系这样一项庞大的工程,我们应当从何入手?我们又该如何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避免对西方框架的依赖?
Does this mean that China’s academic and strategic communities need to be especially cautious when using AI tools? Where should we begin such a massive task as building a governance philosophy and knowledge system tailored to China’s needs? How do we learn from the West while avoiding dependence on Western frameworks?
郑永年:
许多人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使用像ChatGPT这样的工具,这是非常危险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模型的训练方式。
自近代以来,在自然科学领域,最优秀的论文几乎都是用外语,尤其是英语发表的。即使是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往往用英文来发表他们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因为中国学界所公认的顶级期刊基本都是西方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
如今,如果你想利用ChatGPT、DeepSeek或类似工具来构建知识体系,就很难避免被“殖民”的过程。我们必须从源头看起,重新塑造训练模型的内容和方式。
中国有着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这其中蕴含着世界上独一无二、难以比拟的实践经验和历史记录。但要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现代社会科学成果,则需要持续且系统性的努力。
中国在近现代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尤其是四十年间的改革开放。这些跨越几代人的探索和经验,本应成为训练模型的宝贵素材。如果不采用这些经验,模型就仍然是单向的——输入的只有西方的内容而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贡献。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同样强大的中文训练体系,知识生成才可能更加均衡。
我并不是在否定西方。关键在于,当前的社会科学仍然缺乏真正属于中国的“故事”。即使我们尝试讲述中国故事,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却仍然是西方的。中国只是提供了案例和数据——而且很多时候,这种“证明方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理论命题本身就不适用于中国语境。
更危险的是,部分中国学者的目光短浅。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声称已经建立了“自主知识体系”,但他们只是在自说自话。有些经济学教材甚至仅把标题中的“西方”改成了“中国”,这并不是真正的独立知识体系。
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这项工作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更不可能仅靠一两个人完成。
南华早报:您提到,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当从实践出发。那么,您认为中国自身的哪些实践最值得关注?
You mentioned that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should start from practice. Which of China’s own practices do you think deserves particular attention?
郑永年:
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一个例子——它是扎根于实践的。当时,欧洲的革命理论强调城市斗争。但一些失败的经验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进行创新。他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乡村发动革命,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邓小平同样具有创新精神,比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白猫黑猫论”等,都是在具体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突破。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但尚未将其上升为系统性的理论概念。相反,我们往往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自身的实践,但这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两者在根本上是不同的逻辑体系。
社会层面也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实践,比如深圳的发展,就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经验。
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政府与高效市场的结合。我认为这两方面其实在西方经济学中也都存在。而我认为还缺少一个关键要素,那就是“活力社会”(active society)。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其背后往往隐含着与国家相对立的立场。但中国社会从来不是这样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二者是一种连续体。我们的市场与国家也并非截然分离。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绝对私有”或“绝对公有”的概念。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就已经在探索“井田制”,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就在尝试将公有与私有结合起来,而这一点是无法用西方理论框架加以理解的。
南华早报:您也曾提到,打破西方的知识垄断非常重要。在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一些人可能会将此视为中国在争夺全球领导权和话语权。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You also said it was important to break the West’s intellectual monopoly. In today’s tense China-US climate, some may see this as a move by China to compete for global leadership and narrative power. How do you view it?
郑永年:
那是一种用意识形态视角来看待问题的方式。意识形态并不是学者们能够掌控的,我们对此往往只能感到无奈。
我始终主张,我们不是在完全否定西方。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的方法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用这些西方的工具生成出来的概念和理论往往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
正如每个西方国家也都有各自独特的社会科学传统一样,中国应该“借用”西方的方法,而“搁置”其理论建构,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实践,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体系,那将是对全球社会科学的巨大贡献——但这并不是一种对抗行为。
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故意歪曲我们的立场,但我认为,那些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的人只是少数。
主流世界其实已经看到了中国发展的现实与转型,但他们无法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些现象。他们正在等待答案——如果我们不提供,谁来提供?
这既不是要自我封闭,也不是要全面反对西方。光靠一堆人自说自话,既没人听得懂,也没人会接受。
构建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沟通”。我们之所以接受西方理论,并不是因为它们被强加给我们,而是因为它们的逻辑曾经具有说服力。中国也应当构建出同样具有说服力的知识体系,让世界愿意理解并主动采纳。
南华早报:您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重建中国知识体系这一议题,将在“十五五”规划中占据怎样的地位?
How do you expect the rebuilding of China’s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age of AI to feature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郑永年:
我认为构建中国知识体系的进程将会加快,因为这种紧迫性已经非常明显。
我们常说,西方不了解我们,甚至误解、妖魔化我们。现在,我们有责任向西方传播中国声音。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我们不能再让世界一直等待我们的声音。
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开放。西方的知识体系正是在开放中建立起来的,中国也必须如此。一个真正的知识体系,必须是能够被他人所理解的。
另外,我们常常自以为理解西方,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表面。我们确实需要培养一大批通晓多种文明的人才。
我认为现在的处境其实比民国时期更具挑战性。为什么费孝通能够写出《江村经济》?他运用了西方的方法论,出色地解释了中国的社会现象,这其实可以看作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今的中国研究与西方研究是割裂的,而在民国时期,两者是融合的。
当前的学术训练过于强调可量化、可度量的内容——但这些恰恰是ChatGPT之类的工具可以胜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往往是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拥有一个巨大优势:我们拥有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
南华早报:您在新书中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应避免过度关注“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应当如何实现这一点?您为什么呼吁学术界“去妖魔化”?
In your latest book Reconstructing Chinese Knowledge in the AI Era, you raise the need to avoid an excessive focus on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How can that be achieved? Why have you called for a “de-witching” of th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your term for a witch-hunting mindset?
郑永年:
如今,许多人文学者更像是“世俗的祭司”,通过不断生产各种“心灵鸡汤”来迎合大众,这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泛滥。但这对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在西方用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妖魔化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也用意识形态去妖魔化西方,这并不是在构建知识体系,而只是针锋相对的口水战而已。
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价值,是伪学术。它或许一时吸引眼球,但不会留下任何有意义的成果。我们需要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必须回归到基本事实、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
南华早报:中国的智库应如何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回应国际舆论、提升自身影响力?您曾积极评价美国的兰德公司(美国的一所智库),中国的智库可以从中汲取哪些经验?
How can China’s think tanks be developed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international opinion and increase their influence? You have spoken positively about the Rand Corporation in the US. What lessons could Chinese institutions learn from it?
郑永年:
美国拥有西方最为发达的智库体系,而在服务国家利益方面,我认为兰德公司做得是最出色的。
中国的智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背书型”——无论政府让它研究什么,它基本都表示支持;以及“批判型”——凡事都说政府做得不对。这两类智库在现实中都有其存在的空间。
每一个政府都需要有人来评估其政策是否科学。但如果你永远不能说它不科学,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同样地,如果你总是说政府做得一无是处,那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智库。
一个真正的智库,应该是服务国家利益的。而所有领导人,其实也是为了服务国家利益。例如,假如一个香港的智库如果只服务于某位特首的个人利益,那可能会有问题;但如果它服务于香港特区整体的利益,那就是好事。
南华早报:这就让人联想到软实力的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既具有自主性、又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知识体系?
That brings to mind the issue of soft power. How can China build a knowledge system that is both independent and universally applicable?
郑永年:
我认为构建软实力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你写的内容必须有人愿意读;如果没人想读,那就起不了作用;
第二,读者必须能够理解你写的内容;
第三,在理解内容之后,读者愿意接受它们;
第四,不仅接受了,读者还愿意主动传播这些内容。
目前,我们在这四个阶段上都存在问题。但西方在某些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
AI is freeing humans from intellectual labour, which means many people may become unable to think.
我们现在的老师一直在传播西方的知识,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写出能够进入西方课堂的教材?这一点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也许在理工科领域已经有所突破,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呢?
比如,中国在四十年间让八亿人脱贫,这一成就是全球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西方也认可这一点。那么,我们该如何讲好中国的脱贫故事?
我认为,我们应该用学术语言来讲述。如果我们只强调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那肯定无法展现事情的全貌。用政治语言或意识形态语言来讲述,也会让他人难以从我们的经验中汲取有价值的教训。
南华早报:除了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您是否认为人工智能还可能进一步加深国家之间的差距与紧张关系?这是否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Beyond its influence on social structures, do you expect AI to further deepen the gaps and tensions between nations? Could that have an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郑永年:
当然会。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经济秩序,都需要一个基础,就像前三次工业革命一样。在人工智能时代,AI正在成为这个基础,这意味着未来的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都会发生变化。
对此,我持有一定的悲观态度。
前三次工业革命解放了人类的体力劳动,而人工智能正在解放人类的脑力劳动。这可能导致很多人逐渐失去思考能力,形成我所说的“人工智残”(Artificial Ignorance)现象——由于广泛和毫无节制地使用(无论主动使用或被动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所导致的人类自我智力伤害。
中美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存在某种趋同趋势,尤其是在开源条件下,未来内容将会越来越相似。
在AI发展方面,美国受科技右翼影响,基本采取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模式,目前在联邦层面并没有建立起系统性的监管框架。
而欧盟则陷入了“过度监管”的困境,这严重抑制了创新,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局面。
一些欧洲领导人已经呼吁放松监管以扶持本土AI企业,但这将造成两难局面:欧盟一方面希望放松对本土企业的限制,另一方面却又想加强对美国企业的监管,而在欧盟强调规则一致性的前提下,这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中国目前的状态处于美国和欧盟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过度监管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武汉AI初创公司Manus最近迁往新加坡的事件中看出。
特朗普任期内的一个重要改革就是放松对企业的管制,这种科技右翼所倡导的“技术加速主义”正在推动美国的快速发展。
如果美国继续放松监管,而欧盟、中国和印度却没有相应调整,那么我们国内无法落地应用的新兴技术,最终很可能会流向美国——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多年。
中国当然应在环保与劳动权益方面维持必要的监管,但在推动技术落地方面,我认为监管应该适度放松。
否则,大家热议的“新质生产力”就无法真正实现与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国也就仍然会陷于激烈的“内卷”。如果新经济活动更加丰富,内卷现象自然就会减少。
南华早报:在美俄阿拉斯加会晤之后,俄乌冲突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考虑到印度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美印三角关系的力量平衡是否可能出现倾斜?
What changes in the Ukraine war can we expect after the Putin-Trump Alaska summit and how will they affect China? Also, given the tensions between India and Washington, is there a possible tilt in the balance of the US-China-India triangle?
郑永年:
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当前冲突的双方都没有表现出妥协的意愿。欧洲也不会接受“以地换和”的方案,因为这可能会被他们视为一场“噩梦”。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确实是局外人,一方面被这场战争所“绑架”,另一方面在推动战争解决的过程中却完全被排除在外。
Despite signs of decline, the US is still the global hegemony.
关于中国实力的认知存在两种图景。一种是可以量化的,比如GDP、国防发展等,这代表着中国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另一种则涉及到我们如何认知自己,以及他人又如何认知我们。这里就回到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上——这不仅仅是战略思维的问题,也是一种哲学上的问题。
无论是中美俄之间,还是中美印之间,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种固定的“三角关系”。尽管美国有衰退的迹象,但它现在依然是全球霸权。
印度则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策略。尽管近期与特朗普之间出现了摩擦,但总体上美印的关系是在走近的。不过,印度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真正的盟友。印度也在谋求地区霸权,尤其是试图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全球南方”。
我们至今仍未能完全理解或掌握西方的国际关系语言——比如西方语境中的多边主义、联盟体系等。在中国,我们所谓的“伙伴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所说的“盟友”是两回事。
邻里外交也至关重要。中国要在世界上崛起,首先必须在亚洲崛起。正如毛泽东所说,搞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所有人都当“朋友”,往往意味着你没有真正的朋友。
南华早报:中菲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菲律宾也在不断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合作。您曾表示,北京在南海问题上需要保持战略耐心。但近日中方船只在黄岩岛附近与菲律宾发生对峙并发生碰撞,这是否意味着现在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Tens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Manila have been rising. The Philippines has also tightened security with the US and its allies. You have said Beijing needs to maintain strategic pati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oes the recent collision between Chinese vessels during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hilippines near Scarborough Shoal mean it is time for a different approach?
郑永年:
美国的利益已经深深嵌入全球各地,比如欧洲、中东和亚洲。但我们需要接受一个现实:美国既无法被驱逐,也不可能彻底或成功地从这些地区全面撤离。
解决南海争端的前提是要承认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最终的目标并不是要把美国的影响力“赶出”西太平洋。
If both sides deemed the removal of the US from the Western Pacific was the final goal, that might be the worst scenario.
事实上,当美国撤出某个地区时,往往会带来混乱——中东和乌克兰就是例子。那些受影响的国家最终往往还会“请求”美国“回来”。
我们可能需要跳出传统框架,打破一些惯性思维。中国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而过度强调外部势力的威胁,可能并不符合我们倡导的全球化逻辑。我们是否需要进入拉美?是否需要欧洲市场?当然需要——因为我们彼此早已深度交织。
人们对“事实”的认知,往往取决于其思维方式。在我看来,南海争端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头疼问题”。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认知基础,建立互信将变得非常困难。
如果有关各方都把“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视为最终目标,那可能才是真正最糟糕的结果。
就像过去我们允许美军舰艇访问香港一样,我们也可以考虑是否将南海岛礁上的某些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对美方开放。这或许能创造出更多机会,从根本上推动问题的解决。
南华早报:南海争端正因台湾问题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管控局势,避免误判并降低风险?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re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by the Taiwan issue. How can the situation be managed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and mitigate risks?
郑永年:
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战略耐心。
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许多西方人将其解读为“等待复仇”,但这并非其真正含义。它的含义是:在保持克制的同时,寻求一种理性而更优的解决方案。正如李强总理曾说过的,办法总比问题多。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比如西德的做法:它向东德人提供公民身份,为两德货币提供等值兑换,并向西德公民征收5.5%的团结税以支持统一。
我们不会放弃把军事作为最后手段的选项,也必须坚决防止任何“台独”的企图。但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我们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推进统一进程,吸引更多台湾民众。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统一的政治决心,也从意识形态角度讨论了许多问题,但我们很少深入思考应当如何以具体措施推动统一。现在是时候认真思考这些具体路径了。
南华早报:新的K类签证针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人才出台,是否有望有效吸引外国人才来中国?
Is China’s new K visa for STEM professionals likely to be effective in attracting foreign talent to China?
郑永年:
签证政策确实很重要。K类签证只是第一步。从政策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中国首个专门面向人才设立的签证类型。比如美国对不同类型的人才设有多种签证类别。
但外国人才获得K签证之后,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比如如何安顿自己的家庭吸引人才不仅仅靠签证或高薪,更重要的是整体的生态体系,而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We really need an active society. If you rely solely on a government-commissioned institution to tell China’s stories, it will certainly not succeed.
不过,中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教育和人才引进方面,中国肯定会变得更加开放。在“十五五”期间,预计还会出台一系列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新举措——包括关于外资高校在华办学的政策。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也有所差异。循序渐进有其优势,关键是方向必须保持不变。我们应继续稳步向前推进。
南华早报:中国电视剧、游戏和玩具在国际上的日益流行,是否说明放宽监管也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
Does the growing international popularity of Chinese dramas, games and toys suggest that relaxing regulations could also help to tell China’s stories well?
郑永年:
是的。中国故事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包括文字形式以及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形式。而要实现这一点,确实需要放宽相关监管。
我们不能把西方看作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西方社会由多个不同的群体组成,他们的需求也各不相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人以多样化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如果仅仅依靠政府委托的机构来讲好中国故事,那注定是行不通的。
本文译者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