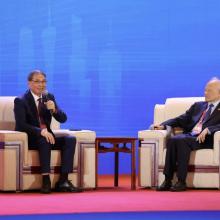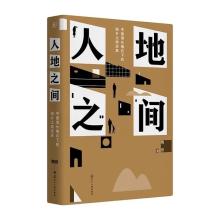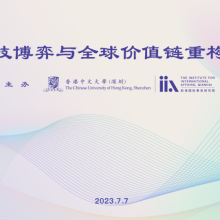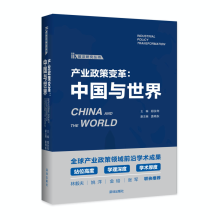編者按: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该地区的严重人道主义灾难,超过6.1万人丧生。由于以色列封锁物资,加之美国与以色列把持援助物资的分发,加沙地带陷入严重饥荒,引发国际社会关切。
8月5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所谓“全面占领加沙”的计划。引起以政府内部尤其是军方的激烈反响。据报道,以色列多名部长称内塔尼亚胡在私下谈话中使用了“占领加沙地带”一词来描述他对加沙地带扩大军事行动的计划。该计划还将涉及以方被扣押人员所在地区。截至目前,以军基本避免在这些地区采取行动。然而,以色列军方激烈反对“接管整个加沙地区”。三天后,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总理内塔尼亚胡关于以军接管加沙城的计划,并批准了所谓结束加沙地带冲突的5个条件。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的是接管“加沙城”,而非内塔尼亚胡此前宣称的控制“整个加沙地带”。
除了来自以色列内部的反对声音外,国际社会也纷纷发声予以谴责。8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以军接管加沙城计划举行紧急公开会议,并得到除美国以外所有安理会成员的支持。其他国家也纷纷表态谴责,包括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德国等代表均发表相关声明。此外,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相继表示将承认巴勒斯坦国。
可以看到的是,在以色列不断紧逼推进强硬占领加沙的背景下,多个在过去一直避免在巴以问题上表态的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明显转向。国际社会要求落实“两国方案”的呼声进一步加强。
以色列一意孤行占领加沙,背后存在何种考量?又可能会付出怎样的占领成本?本文深入剖析以色列重占加沙的复杂考量与潜在后果。文章认为,面对高昂的加沙全面占领成本,以色列领导层似乎更倾向于一种“部分控制”策略——即占领关键节点以实现“行动拒止”,却刻意规避加沙地区的治理责任与人道义务。然而,以色列过去占领加沙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已证明,占领只会陷入消耗与反噬的恶性循环。在国内政治层面,内塔尼亚胡则要面对迫近的2026年大选带来的政治周期波动,反对派的上台有可能撕裂任何需要长期投入的占领战略的延续性。外交上,重占行动正加速消耗以色列宝贵的国际资本,将其推向外交孤立的边缘,西方传统盟友的疏离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条件的硬化,预示着以色列将面临深刻的战略消耗。
以色列“全面占领加沙”的行动必须直面的现实是:加沙地区如此高昂的代价是否真能换来持久的安全?抑或只是为该地区开启下一个更危险的循环?

*本文原载于《地缘政治观察》(Geopolitical Monitor),原题为“Israel Gaza Reoccupation: Costs, Consequences & Calculus”,供读者参考。
引言
以色列正在考虑重新占领加沙地带,但不应该将此行动简单地理解为一次草率的政治动作。相反,这一思量是以色列对构成其运作环境的结构性压力和持续不安全感的理性回应。2007年以来,由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区一直是周期性火箭弹袭击和心理战的基地。2023年10月,由哈马斯所领导的袭击更对以色列威慑姿态进行了重大“破防”——这次袭击不仅造成平民伤亡,还公开暴露了以色列的脆弱性。
在缺乏能够强制执行和平的中央国际权威的情况下,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军事能力来维护主权。对以色列而言,这意味着在其认为存在迫在眉睫或持续威胁的环境中采取果断行动。在此背景下,重新占领加沙虽然代价高昂,但被以色列视为消除哈马斯基础设施并重建威慑力的必要措施。
即使以色列面临日益增长的外交反对和国内经济疲态,这种逻辑依然存在。从系统性角度看,以色列无法依赖国际社会来消除威胁或重建威慑力。即使是长期盟友例如美国,对以的政治支持水平也起伏不定。在这些条件下,单方面军事行动成为一种在结构上合理(尽管在政治上存在争议)的确保安全的手段。
以色列通过避免阐述清晰的战后愿景,保留了在快速演变的战略背景下灵活行动的能力。这种战略模糊性并非缺陷,而是一种特性,它为决策者预留了调整行动的空间,而无需预先承诺一个政治上有分歧的最终结局。
一、结构性疲态侵蚀军事能力
以色列国防军(IDF)是一个拥有先进技术能力的强大机构,但它也无法免于疲惫。与大国专业的常备军不同,以色列国防军严重依赖平民征召的预备役人员,而其中许多人在加沙战役期间经历了反复的部署。随着战争正迈向第二个年头,来自内部的压力正与日俱增。
预备役人员正表现出心理疲劳和抗拒的迹象。自杀报告和对人员再次部署的普遍抵制展现出军队出现了系统性的过度扩张。这种内部带来的压力削弱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并引发了广泛质疑,即军队在没有重大重组或增援的情况下是否有维持长期占领的能力。
由于以色列在多条战线上存在军事责任,情况也进一步复杂化:黎巴嫩的真主党、叙利亚的代理人、约旦河西岸的不稳定局势,以及持续与伊朗的战略竞争。每一项威胁都需要投入资源和关注,使得以色列国防军的注意力分散,并让其人力和后勤能力愈加紧张。
来自军队内部的制度性反对,尤其是来自总参谋长埃亚勒·扎米尔(Eyal Zamir)等人物的反对,也反映出内部对成本的考量。抵制重新占领加沙这一态度并非植根于和平主义或外交,而是出于行动的现实主义考量。军事领导层认识到,占领加沙可能会转移关键资源,削弱以色列国防军在其他战线上的威慑姿态,并导致一场没有明确终点、低收益、高风险的行动。
二、对加沙的“部分控制”:规避治理的遏制策略
鉴于全面占领加沙在人力成本和政治资本方面会付出巨大代价,以色列似乎正倾向于一种“选择性领土控制”的战略。这种设想并非是在加沙全面恢复治理,而是占领关键的基础设施点:包括道路、过境点和补给路线。
这一战略旨在通过防止武装派系巩固领土或将其用作集结地来实现行动阻断,同时刻意避免承担民事管理的责任。以色列将寻求仅保留军事必需区域的控制,而允许其他地区存在治理真空和人道状况恶化。
这一战略也反映出以色列刻意的权衡:通过只占领加沙地带的部分区域,以色列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部队投入和财政负担。它的目标并非促进加沙的稳定,而是管理和遏制,优先通过分裂和破坏而非重建或长期发展来压制威胁。
然而,这种模式带有结构性风险。安全领域的真空会招致进一步的不稳定。在无人治理或巡逻不足的地区,武装团体可以重新建立行动并重建网络。此外,这些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引发地区溢出效应,可能将外部行为体卷入冲突,或加速外交上的疏离。
实际上,这种模式优先考虑“战术控制”而非“战略解决”,是一种风险管理而非冲突解决的权宜之计。
三、以史为鉴:控制领土无法根除抵抗活动
以色列从1967年至2005年在加沙的历史经验,为评估当前的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此期间,以色列军队在该飞地保持了直接的军事存在,直面对以抱有敌意的人群,经历了反复的起义(第一次和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并付出了重大的军民伤亡。
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清晰:占领的代价远远超过了战略收益。人口结构的平衡(日益年轻化和贫困化的巴勒斯坦人口)使得占领难以为继。2005年时任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领导下的单方面撤离是对战略过度扩张的冷静评估。这一决策背后是一种认识,即继续在加沙的存在将耗尽以色列的安全、政治和经济资源。
如今,推动重新占领加沙的意识形态动力主要来自极右翼派系。他们不顾人口现实或军事可行性,将加沙地带视为历史犹太家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执着与先前占领的教训格格不入,可能重蹈覆辙:军事控制激发的是无尽的抵抗,随后引发新的叛乱,同时收获极小的战略稳定。
因此,以色列领导层将面临一个核心悖论:他们渴望对一个历史上以持续抵抗为典型特征的领土施加控制。历史表明,军事优势并不能保证安全,在外部审视和内部异议的条件下,试图重塑人口结构或压制当地居民政治认同的努力很少能持续。
四、外交孤立:升级占领的必然代价
重新占领加沙不仅会带来以色列国内和军事行动上的代价,还会带来重大的外交风险。如今,包括加拿大、法国和英国在内的主要国际行为体已表现出对以色列在加沙战略的不满。这些国家正日益倾向于承认巴勒斯坦国,而在此地区进一步的升级可能会加速此类行动。
这也体现出以色列战略环境外部平衡的变化。历史上,西方盟友的外交支持既为以色列提供了合法性,也使其获得了关键的军事技术。但随着这种支持的削弱,以色列在国际体系中有被重新定位为“贱民”国家而非可靠安全伙伴的风险。
阿拉伯世界也在重新调整对以色列的态度。即使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最近正寻求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国家,也在叫停对以的重建援助,并为未来的合作设定前提条件,即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些变化限制了以色列的行动自由,并在其寻求巩固地区影响力的关键时刻增加了外交孤立的风险。
以上压力所带来的累积效应会成为对以的战略消耗:以色列国际地位、经济关系以及通过联盟投射力量的能力逐渐被侵蚀。与日常可见、可感的军事成本不同,外交成本是无形累积的,直到达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此时国际共识通常会不可逆转地转向孤立和制裁。
五、政局不稳:选举周期撕裂战略延续性
除军事、外交外,以色列的战略规划也日益受到2026年大选临近的影响,外界普遍预期此次选举将导致政府更迭。当前的民调显示,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领导的联盟不太可能获得多数席位,出现一个具有不同优先事项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新政府的可能性愈发上升。
选举带来的压力也暴露了“重新占领”战略在时间上的脆弱性。它需要持续多年投入的军事行动,如果没有广泛的跨党派支持,就无法在连续的政府周期中维持。然而这种支持并不存在。政治反对派的关键人物,包括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已经公开批评重新占领的前景,并呼吁重新回到外交解决的道路上。
选举局势不稳意味着,倘若以色列于2025年开始重新占领加沙,也可能在2027年放弃或局势被逆转,留下一地鸡毛——混乱的安全局势和士气低落的军队。这将与2005年撤离后的后果如出一辙,而那次撤离加沙为最终哈马斯得势营造了环境。
"Israel’s leadership is thus confronted with a central paradox: the desire to impose control over a territory historically marked by persistent resistance."
此外,以国内的政治动态也在积极干预塑造战略决策。内塔尼亚胡所设计的剧本中可能包括一种假设,即军事升级可以巩固公众支持并阻止政治崩溃。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政策正与政权生存的渴望彼此纠缠,扭曲了战略清晰度,更偏向于一种短期的政治定位。
最终,政局的不稳定将营造一种不断循环的政策环境:长期目标屈从于选举的权宜之计,战略抉择随执政联盟更迭而脆弱易变。
本文译者
周宇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IIA学术编译组成员。
GBA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