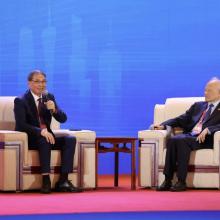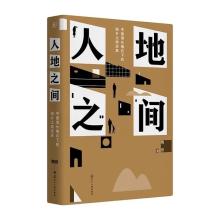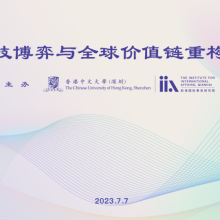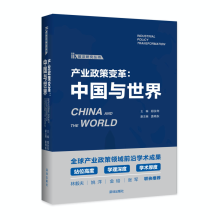編者按: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以减税为核心、削福利为配套的“逆向再分配”,加剧贫富分化,引争议无数——或斥其倒退,或疑其针对中国。然深究其里,这既关乎特朗普阵营对传统美国定义与变迁,也关乎亨廷顿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文化冲突与国家认同。
法案的推行,伴随着清晰的“牺牲”图谱:国内削底层福利、撼民主党根基、抑激进思潮;国际弃盟友、破旧序、滞发展中国家前路。只是,政治碎片化、资本失控、技术冲击与政府角色迷思,让这场“里根革命2.0”充满变数。当技术颠覆就业、政府角色被刻意弱化,特朗普的“美国梦”或许只是一场豪赌——赌注是整个社会的撕裂与全球秩序的动荡。
这不仅是法案之争,更是“谁的美国”之争。答案,仍在风中飘荡。
一、“大而美”法案的核心内容与争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7月4日签署“大而美”法案(OBBB),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人们普遍认为,“大而美”法案本质上是一次以减税为核心、以压缩社会保障支出为配套的财政重构工程,因此展现出高度结构化的“逆向再分配”特征。
的确,很多数据都指向这个方向。法案将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多数条款永久化,未来十年减税规模高达4.5万亿美元,其中企业与高收入群体获益最大。与此同时,约1.7万亿美元的财政缺口将通过削减底层民众依赖的福利项目填补:包括对医疗补助(Medicaid)和食品援助(SNAP)实施新的工作门槛、设立联合支付机制、推动各州分担SNAP误差成本等,预计将有1180万人失去医保,另有300万人失去食品援助。法案对老年人、残疾人和低收入家庭的制度性支持空间被显著压缩,但对高净值人群和资本收入减税条款却得以延续乃至扩大。据耶鲁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估算,未来十年,美国收入最低20%人群的年均税后收入将下降2.9%,而最富裕20%人群将上升2.2%,贫富分化在税制层面被制度性固化。再者,大学捐赠基金课税上调、汇款附加税、清洁能源补贴取消等条款,都将影响教育、环保与移民群体的可获得性与权利保障。
因此,整体上看,该法案以牺牲基础公平为代价强化“选民经济”,重塑美国社会分配格局,其政治本质是对“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模型的系统拆解。
如果从这些角度看,这个法案无疑是倒退的,甚至是落后的和反动的。一些批评者更是“无中生有”地认为,这部法案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而是“让中国再次伟大”。(当然,在中国,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针对中国的法案!)
二、法案的政治本质:“美国保卫战”
不过,一位朋友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他拜访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多所大学,和那里的教授们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被多次告知,特朗普所进行的是一场“美国保卫战”。尽管这场“美国保卫战”很难如特朗普所愿那样进行下去,但的确是“特朗普(们)”“保卫美国”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一观点尽管没有在西方流行开来,但较之任何其他观点都更为深刻,直指“大而美”法案的本质。也就是说,讨论“大而美”法案不仅仅要看法案本身的条文,更需要理解其背后的议程,即“美国保卫战”。
1. 传统美国定义与变迁
说其是“美国保卫战”,那么问题在于“保卫什么样的美国?”这里的“美国”由谁来定义呢?特朗普是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产物。他的第一次当选被普遍视为是美国白人(即MAGA运动的支持者)的公投。那么,人们不妨从这些“白人”的角度来定义他们所认知的“美国”。
今天人们所见到的美国由17世纪从英国出发的清教徒定居者所创建。此后,不同国家的移民来到美国,但当他们来到时,美国已形成了盎格鲁—新教文化。21世纪前美国的移民一直不占主流:从1820年到2000年,外国出生者平均仅略高于全国人口的10%。
因此,美国的文化主体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其主体要素包括:英语、基督教、英式法治理念、司法、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和个人权利理念;新教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工作道德;源自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和音乐传统。
正是因为美国是个移民社会,并且大都是反抗旧制度或者对旧制度不满的移民,因此,美国人形成了特有的所谓的“美国信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兼有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制等。与母国文化相比,美国清教徒的持异议色彩带给了美国信念的更加“强烈自由精神”。
在过去,人们经常用“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缩写),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来形容美国。《剑桥词典》把此解释为“祖先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白种人,也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中势力最强大、最富有的白人”。
这个概念最初(1957年)由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Andrew Hacker)所使用,但当时的“W”代表“Wealthy(富有)”而非“White(白人)”,后来的人们则以“W”来指称白人。不过,这一字之改,使得这个词更直接指向了这个群体的种族本质。德国社会学家维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是在信奉新教伦理的人口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 亨廷顿理论视角下的美国文化冲突与国家认同挑战
但是,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国已经不是原来的美国,所有这些传统特征不再能够定义美国。不仅如此,这些特征的“流失”被视为是已经威胁到人们传统所认知的“美国”的存在了。
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文化多元主义盛极一时。尽管对多元文化论题的讨论不时在美国发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但“左派”沿着这个思路不断发展,形成了今天特朗普阵营所竭力反对的“多元化、公平与包容”(The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DEI)。
不过,更早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系统论述和质疑的是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93年,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亨廷顿在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即刻在美国内外引发巨大而持续的讨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在苏联解体之后,伊斯兰必将成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的最大阻力,因此,西方的下一次大战对象必然是伊斯兰世界。
1996年,在此基础上扩展,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 在这本书中,亨廷顿再次强调,苏联解体之后,冷战期间资本主义的西方集团和共产主义的东方集团之间的冲突会被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取代。亨廷顿界定了9个主要的文明,包括1)西方;2)拉丁;3)伊斯兰;4)中华;5)印度;6)东正教;7)日本;8)非洲;9)佛教。他认为,要理解当前和未来的冲突,就必须理解文化冲突,“文化”(culture)——而非“国家”(the State)——成为战争的理由;如果西方不承认文化紧张的不可调和性质,那么西方就不可避免失去其主导地位。因此,亨廷顿建议,西方必须从文化上强化和巩固自身,而放弃“民主普世主义”和对他国的军事干预。
在很大程度上说,亨廷顿的著述是对其学生福山(Francis Fukuyama)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的回复。在“历史终结论”中,福山认为,苏联集团解体之后,西方民主就可以终结历史了,即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所能拥有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政体。现在看来,亨廷顿是正确的,而福山则是错误的。
亨廷顿并没有就此为止。2004年,他出版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即《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将“文明冲突”观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论述了“美国国家认同”所受到的种种“挑战”,并把此提高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亨廷顿明确指出,美国认同在迅速减弱。从历史上看,美国的认同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或者说,对一个国家的认同(即所谓国家凝聚力)一般由种族、民族、领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组成。但是,在美国,对国土自豪的人,仅有5%,对政治体制最引以自豪的美国人有85%。可见,对于美国人来说,意识形态重于疆域。人种和民族单一的美国不复存在;美国的文化受到解构主义的攻击;美国认同只剩下意识形态。但苏联的解体表明,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弱的。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永恒的。正如卢梭所言,“既然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国家能希望永世长存呢?”即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候遇到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胁,或是受到更加激烈和无情的外部“野蛮”势力的威胁。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最终也会遭受斯巴达、罗马等国家的命运。
亨廷顿进而认为,尽管美国社会的生存受到严重挑战,但通过重新振作国民认同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能够推迟其衰亡,遏制其解体。
概括而言,亨廷顿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外部的苏联集团,那么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则主要来自美国内部。
如果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理解MAGA运动和特朗普的“大而美”法案是否可以看到其更为深一层次的含义呢?
三、法案隐含的“牺牲”
尽管特朗普自认为其有“神助”,但他还没有把自己视为神。要重振美国,他需要依靠力量。重振的过程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有牺牲者,也有获得者,牺牲者的反面即是获得者。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无论是牺牲者还是获得者,都表现得清清楚楚。
概括地说,“大而美”法案隐含着美国内部的三个相关的“牺牲”和外部的三个相关的“牺牲”。
1. 美国内部:三个“牺牲”
在内部,第一个最大的“牺牲”便是美国的“社会底层”。正如前面所论及的,这一点人们都看到了。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特朗普并非要牺牲整个社会底层,因为他宣称他要代表美国大多数劳工基层的利益。在“大而美”法案里,他要牺牲的是依靠福利而生存和生活的社会底层。特朗普反对欧洲式的福利主义。如同新教理论,特朗普相信人们所获得的应当是人们努力的结果,而非天生的“权利”,更不是不劳而获。因此,在削减福利的同时,特朗普也免去了“小费税”,鼓励底层人群通过工作而有所获。这一思路和传统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强调资本的作用,强调“一次分配”而非政府的“二次分配”在增进全社会利益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个“牺牲”是美国的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说,“大而美”法案是对民主党的所有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反动。这不仅表明今天美国政党政治的撕裂程度,更重要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何谓美国?”的完全不同的认识。
第三个“牺牲”是极端或者激进力量。极端的“左派”必然是被打压的对象,尤其是大学。特朗普对哈佛和哥伦比亚等大学一直充满敌视,认为这些大学并没有培养出美国所需要的人才,而是充斥着LGPTQ文化、“觉醒”文化和DEI文化,从而培养了反美国的“人才”。特朗普的这种反对充分表现在“大而美”法案系统性削减联邦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向精英阶层倾斜的趋向性。据New America估算,法案对教育整体削减额度达3500亿美元,其中3000亿集中于高教与贷款系统。这一财政重构通过如下机制推进:一是对佩尔联邦助学金(Pell Grant)项目附加严苛的修课要求,显著提高获取门槛;二是取消联邦研究生贷款(Grad PLUS)和家长贷款(Parent PLUS),设定研究生贷款上限(硕士10万美元、博士20万美元),大幅削弱中低收入家庭尤其是少数族裔获取高等教育的能力。穆迪预测,美国最古老并且规模最大的非裔高等健康科学高等学府梅哈利医学院(Meharry Medical School)将因本土生贷款额度受限与国际生拒签率高达42%的双重冲击,陷入高达3700万美元的年度赤字,这显示出高教财政高度依赖政策设计的系统风险。
因此,有批评者认为,法案的推出是一场以财政与问责为手段、以意识形态重塑为目标的政治清算。或者说,特朗普想用他认为的“美国的意识形态”来替代他认为的“非美国的意识形态”。特朗普政府在教育领域推行的政策体系——从削减拨款、问责绩效,到打击国际生与特定高校——构成一场有组织、有目标的“去精英化”行动。此前特朗普政府通过将联邦资助与高校政治倾向挂钩,以“反犹”“亲巴抗议”为由,冻结常春藤高校拨款,要求其提交学生社团记录与课程审查材料,甚至签署“忠诚声明”。这些本质上是以国家安全名义推进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治理,打击自由派主导的学术机构与优绩主义网络。教育部权威被削弱,多元、平等、包容议程遭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大学从知识与批判的空间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延伸。法案通过财政杠杆和绩效问责掩盖其政治本质,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制度性调整重塑教育的意识形态属性,让大学不再是多元与批判的空间,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2. 国际层面:三个“牺牲”
在国际层面,第一个“牺牲”便是盟友。这很容易理解。特朗普认为,美国的盟友高度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愿意出钱支持美国,这造成美国内部发展和外部霸权的不可持续性。尽管传统上美国精英认为,基于美国盟友体系之上的“自由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的基础,但特朗普对此并不感兴趣。无论在国际安全层面还是在国际经济层面,特朗普完全背离了传统的同盟政策。这使得整个西方感到绝望,认为特朗普导致了“自由国际秩序”的解体。
与盟友体系解体相关,第二个“牺牲”是国际秩序。从其第一任期到今天第二任期,特朗普已经从联合国各个功能部门(例如教科文组织)和诸多国际条约(例如巴黎气候协议)“退出”,同时也把被视为是国际经济秩序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搁置一边。尽管美国在二战之后在确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方面扮演了主导角色,但特朗普认为,这一秩序多年来已经演变成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利益。
第三个相关的“牺牲”便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无论是特朗普的大规模反移民政策还是其“再工业化”政策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美国一直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政策有助于美国的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辅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输送了大量的留学生人才,尽管很多人学成之后留在美国为美国做贡献,但也有很多学生返回了他们的母国,推动了母国的经济发展。特朗普的教育政策不仅对少数族群不利,更不利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同样,特朗普的“再工业化”政策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这些国家的“去工业化”。二战以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了欧洲的复兴,也帮助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实现工业化。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是在继续通过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来实现工业化,而美国往往是这些国家的最重要出口国。特朗普的“再工业化”政策无疑决定了美国不再是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助推力量,而是阻碍力量。
简单地说,特朗普“大而美”法案想回答一系列相关的大问题:谁的美国?谁是美国的统治者?美国向何处去?
四、“大而美”构想所面临的挑战与不确定性
尽管这一法案遭到了最强有力的批评,甚至妖魔化,包括美国国内的左派力量,也包括来自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对力量,但从美国民主党溃不成军的现状来看,这一法案还是具有相当的支持力量的。因此,问题不在于这部法案的产生是否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在于是否能够真正落实下去而实现特朗普“大而美”的构想。有很多问题可能是特朗普回答不了的。
1. 美国政治的碎片化
首先是美国碎片化的政治。在所有国家,政治决定一切。美国政治的碎片化不仅仅表现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党政,更表现在两党内部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民主党内部是碎片化的,共和党内部也是碎片化的。最近亿万富翁马斯克因为和特朗普闹不和成立了新的政党,“爱泼斯坦文件”也导致着特朗普和MAGA运动的分裂。政治的碎片化表明这些力量都可以随时分化和整合。尽管在制度层面,正如很多观察家所已经指出的,现在的美国趋向于“三权合一”,而非传统上的三权互相制衡,特朗普似乎掌控了大权,但政治碎片化并非是特朗普所掌控的。实际上,在任何国家,民粹政治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易变性。特朗普通过民粹政治而掌权,但如果掌控不好,他也是可以被民粹政治所冲垮的。
2. 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其次是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并非特朗普所掌控。特朗普想在最大限度上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创造财富,在这个基础之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和培植美国的“白人中产社会”。但是,这里的风险极高。今天美国的问题本身就是因为资本坐大所致,特朗普的政策赋予资本更多的权力和权利,这可能不仅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恶化。正如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所指出的,“别想指望这份法案带来美国经济繁荣增长”。
3. 技术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技术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互联网(平台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不仅在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的消失,而且在促成财富掌控在社会绝少数个人手中,即那些“巨头”手中。尽管特朗普“大而美”法案希望能够再次做大白人中产,但当代技术的发展对白人中产同样不友好。
4. 政府的角色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角色。特朗普想通过对资本的“去监管”和对地方政府的“分权”去构造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这是1980年代里根革命的理想,也是现在特朗普改革的理想。但问题在于,今天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里根革命1.0版”的产物,作为“里根革命2.0版”的特朗普革命可以解决“里根革命1.0版”所产生的问题吗?无论是里根革命1.0版还是里根革命2.0版,都没有触及美国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问题,而是强化了美国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
如果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美国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其问题在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关系都是政治,而政治的核心就是政府。想通过消弱政府的力量来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问题,无疑是南辕北辙。
GBA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