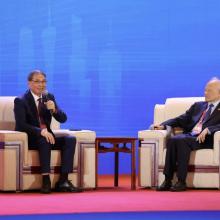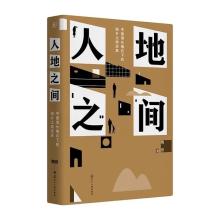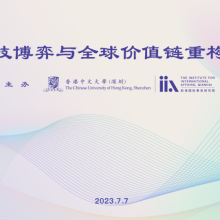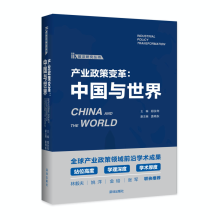編者按:当奥本海默目睹第一朵核蘑菇云升起时,他引述《薄伽梵歌》:“我已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八十年后的今天,这句预言正以更复杂的方式应验——核威慑的悖论日益凸显:人类发明终极武器以求安全,却陷入更深刻的不安。乌克兰弃核的惨痛教训、伊朗核设施遭袭的连锁反应、美传统盟友纷纷寻求核武自保,无不揭示一个残酷现实: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核按钮正从终极威慑沦为生存必需品。
美国从“核保护伞”提供者转向“毁灭性”战略,加速了全球核秩序的变化。现今,韩国七成民众支持拥核,核技术门槛因AI发展持续降低,我们正目睹一场史无前例的安全范式崩塌。若全球化退潮、主权壁垒高筑,世界将迎来“死神”世纪,还是孕育出新安全架构?
本文深刻探讨了核武与安全问题的由来、发展与未来。作者提出警示:人类在发展核武器技术方面的能力在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对应对核武器的手段越来越弱化。如果目前的趋势不能得到逆转,那么在可见的未来,现在人们所见的“国际社会”会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近代之前的帝国时代。
引言
自有记载的历史迄今,“安全”始终是一个有组织社会所追求的最低目标。如果不能实现这个最低目标,“死神”随时会降临这个社会,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同时,对安全的追求也成为了人进步的一大动力。1832年,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在当年出版的《战争论》中总结说,“为了对抗敌对的力量,力量用艺术和科学的发明来武装自己”。1945年7月16日,“原子弹之父”之一、美国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在观看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的第一次核武器试验成功时深受震撼。美国原子弹是当时美苏安全竞争的产物,照理说奥本海默完全可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格言来给自己“盖棺定论”,但是奥本海默没有这样做,而是引用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里那句“而此刻我已变做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科学和艺术可以创造“力量”,但“力量”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不再是科学家和艺术家所能掌控的。自从被称为“死神”的核武器技术发明以来,距今已有八十年的历史。从理论上说,任何有工业基础和意志的国家都可以掌握这一技术。尽管经验地看全球真正拥核的国家始终只是少数,但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想拥有这一技术来实现“安全”这一最低条件。但是,荒唐的是,就大趋势而言,人类不仅没有因为发明核武器而变得越来越安全,而是相反,即越来越不安全了。
可以预见,美国对伊朗境内三个核设施实施的打击行动势必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的新一波核扩散运动。人们迄今还不能证实美国的打击运动是否真的成功了。但即使假定美国的行动如特朗普所言是成功的,那么这一攻击行为也只会加快而不是延缓核武器的扩散。
一、以“核武”谋“安全”
自核武器被发明以来,人类发明了几种方法来求得自身的安全。
1. 主要核武国家之间的核威慑
第一种方式是主要核武国家之间的核威慑,尤其是敌对双方之间的核威慑。根据1968年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有五个国家被正式承认为合法的核国家,即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英国,这五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除此之外,还有四个没有加入该条约、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进行核试验;朝鲜在2006年首次引爆核弹;而以色列——其核计划始于上世纪60年代并得到了法国的支持——被广泛认为至少拥有90枚核弹头,尽管该国在政策上一直对其核地位保持战略模糊。
在这些国家之间,核威慑主要表现在冷战期间的美苏两国之间。学术和政策界对美苏两国间的核威慑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概括起来无非就是美苏两国可以确保互相毁灭。也就是说,核武器的“死神”功能有效地遏制了这两国使用核武器。的确,自核武器发明以来,除了美国在二战后期向日本投了两颗,还没有第二个拥核国家使用过核武器。
经验地看,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两国不断摸索出“和平共处”之道。尽管两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不断,但美苏两国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冲突。所谓的冷战也只是“冷和平”。
2. 防止核扩散
防止核扩散主要是指已经拥核的国家防止这一技术向其它还没有拥核的国家扩散。但这一方法并不能总是有效的,因为经验地看,拥核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只要任何一个国家认为有能力或者有潜力的,那么其必然想实际拥有这一技术。实际上,对很多国家来说,是否拥核已经成为自己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志。
其次,尽管存在着像联合国那样的国际组织,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并没有改变,各主权国家的“自保”性质也没有改变。因此,一旦当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时,就会产生发展核武的巨大动机和动力。
再者,地缘政治之争给一些拥核国家以“正当”的动机来变相地输出核技术。例如,美国为了扶持印度来应付中国,通过不同途径向印度输出核技术。
3. 核保护
这种方式往往发生在同盟体系之中,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中。美国承诺对其同盟国家提供核保护。只要被保护国家觉得自己是受到保护的,安全是有保障的,那么这些国家就不会有很大的动机来发展核武器。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两个拥核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战争,但是核武并没有消除战争。除了拥核国家之间的代理人战争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拥核国家对另一个不拥核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就是核威慑下的常规战争。俄乌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拥核的紧迫感而言,这场战争对今日世界的安全局势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而美国近日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更是加重了这种紧迫感。
二、俄乌战争对“核威慑”涵义的深刻影响
不管俄乌战争有什么样的根源,这场战争对核武器的未来具有深刻的涵义,至少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这是一场一个拥核国家对一个非拥核国家的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核国家占据了战场上的优势。第二,如果把乌克兰所进行的这场战争理解为拥核国家(即“北约”)的代理人战争,那么两个拥核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和战争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相互毁灭”的威胁下,谁也不敢动用核武器,但在核武器的威慑下常规战争照打不误。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获得独立。俄罗斯迅速将战术核武器从乌克兰领土撤出,但乌克兰仍然实质掌握着约1800枚战略核弹头以及战略轰炸机和洲际导弹。就核弹头的数量而言,乌克兰是当时世界上第三大核武库。尽管当时的乌克兰尚无独立发射核武的能力,但因为乌克兰本身就是苏联重要的军事工业中心,被普遍认为乌克兰拥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对弹头进行改装,从而实现完全掌控。
当时的美国则希望尽快消除这些核武器,因为在漫长的冷战期间,在乌克兰的这些武器原本的设计、建造和部署目的大都是针对美国和为了摧毁美国城市的。因此,当时美国的重点是确保刚刚独立的乌克兰将其庞大的核武库移交给俄罗斯,而当时的俄罗斯被美国视为朝着西方式民主政治发展,今后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
对刚刚独立的乌克兰而言,其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没有力量应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最终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同意将全部核武器转交俄罗斯。作为交换,美国、俄罗斯和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承诺尊重其独立和现有边界。
但俄乌战争不仅让乌克兰后悔莫及,而且也让更多的国家改变了拥核的看法。人们的一个普遍假定便是:如果当时乌克兰坚持一下,最终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会发生之后的俄乌战争吗?或者俄乌战争会进展到现在这种程度吗?2023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接受爱尔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对当年迫使基辅(乌克兰政府)放弃核武器感到“非常后悔”,并暗示如果乌克兰保留核武,俄罗斯可能根本不会发动入侵。
在很多人看来,在一个基本上依然是“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从法国总统戴高乐到今天朝鲜的金正恩的选择是对的,而乌克兰的选择则是错误的。戴高乐在1960年代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远见决策,即发展完全独立的核能力,而不是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尽管当时的法国也是美国的盟友,但戴高乐并不相信美国的核保护,他要把核武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戴高乐的这一选择当年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但戴高乐坚持下来了。尽管时代不同了,朝鲜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多年来,朝鲜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不愿动武的心态,成功发展出核武,成为足以挑战全球安全的国家。当然,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和韩国相信美国会向他们提供核保护。
今天,伊朗的“不幸”在于以色列。以色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宣称其目的是阻止伊朗实现“核突破”。而以色列则有效和巧妙地利用了其和美国的特殊关系,让美国以这样一种方式卷入这场战争。
假定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的打击是真实的,那么对面临生存威胁的国家而言,现在必须在两个问题之间选择一个,即,必须拥有核武器才能自保?或者,追求核武器太危险,反而可能提前遭到打击?尽管这两个问题都是真实的,但在一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里,更多的国家会选择第一个问题。从戴高乐到金正恩,他们学会了应当选择哪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人们看到,一方面美国宣称已经摧毁了伊朗的核野心,另一方面伊朗则宣称恢复追求核技术的努力。
三、美国外交政策演变对全球核安全的冲击
促成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的因素有很多。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很显然,前述核武世界获取安全的三种方式,即核威慑、防止核扩散和提供核保护,都与美国有关,甚至由美国主导。美国外交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在诸多变化中,就核武来说,有两个变化趋势是关键。
1. 美国力量性质的演变
美国从二战之后从一个被称之为“建设性”力量演变成一种“毁灭性”力量。二战之后,无论是占领德国(西德)还是日本,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建设性”的,即要把这些国家建设成美国可以接受的西方国家。这种战略意图也反映在美国的经济外交上,无论是战后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还是之后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的扶持。美国在帮助这些经济体发展的同时,也发展出了控制他们的有效体制和机制。
但是,自从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很快演变成一个“毁灭性”力量,即美国开始不再强调通过占领或者派出地面部队进驻被侵略国,而是对被侵略国的重要设施,尤其是军事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摧毁之后就回撤。对一个拥有最强大毁灭性武器的美国来说,这种战略也是有效的,即摧毁对方,消除对方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之后的克林顿也承继了这种毁灭战略,表现在北约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尽管在这场战争中,北约的说辞是“人权高于主权”,但其战略的本质是毁灭,而非建设。
但是,进入小布什时期,美国新保守主义崛起——这是一种带有强烈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开始的时候,新保守主义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但随后的“9·11”恐怖主义事件给美国予沉重的打击,新保守主义就演变成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即推翻被美国界定为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占领该国家,企图把该国转变成为美国式民主国家。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再到拜登,美国基本上都推行这种占领战略。但是,这种战略不仅成本极高,而且是彻底失败的。因此,拜登执政时期,美国撤出了驻阿富汗的美军。俄乌战争发生以来,即使美国深度介入这场战争,但并没有派遣美军进入乌克兰,而是维持了代理人战争的性质。
特朗普这次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可以被视为是“毁灭战略”的回归。特朗普对推行传统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在内部,特朗普政府已经关闭了部分负责专门推行美国价值观的“国际发展署”。在外部,这充分表现在他把中东的访问定义为“招商引资”外交,而非政治外交。并且他直接批评了美国此前对中东的政策。再者,他也不喜欢战争。他多次说过,美国把中东轰炸了个遍,中东得到什么,美国得到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忽视了美国的安全利益;相反,如果特朗普感到美国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他同样会使用“毁灭战略”。
2. 特朗普的“退群”策略
这一策略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特朗普政府从诸多联合国体系的功能部门退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条约等。尽管二战之后,美国本身在确立联合国体系中扮演主导角色,但特朗普认为,这一体系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第二,特朗普甚至不再重视美国霸权赖以生存的“联盟体系”,即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作为这一秩序的主导者和领导者,美国一直承担着为这一秩序提供“国际公共品”的责任,主要表现在美国为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和提供安全保护。提供核保护伞也是这一秩序的重要部分。特朗普认为,这种美国提供“国际公共品而其他国家搭便车”的体系安排在使得美国不断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务的同时大大增加了美国的负担,是美国衰落的一大根源。
在这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的一系列表述更为系统。万斯5月23日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向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生致词时,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新的美国对外战略思维,他强调未来美国动用军事力量时会更加谨慎,避免卷入看不到终局的战争之中,美国将回到以现实为本和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
万斯批评了美国以往的对外政策,指出一些美国总统卷入对美国国安和核心利益并不紧要的海外冲突,牺牲自家国防和对盟友的维护,转而扶持其他国家建国和干涉他国事务。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没有对手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以软实力取代硬实力,停止生产汽车、电脑,乃至于武器,比如保护海域的船舰等。美国领导人追求他们认为会是很简单的任务,像在中东建立民主等,结果发现不仅困难重重,也耗费大量资金,得不偿失。
再者,万斯也认为,美国主导地位不受挑战的时代已经结束,正面临来自其他大国的严重威胁。过去的美国政府没有留意大国竞争,也没有为同等竞争者的出现做好准备。美国称霸海空和太空的时代已结束,美国主导地位不受挑战的时代已成过去,美国及美军人员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因此,美国今后要把重点转向国内,尤其要在科技领域保持领先优势。
针对来自国际的威胁,万斯强调:“这并不意味我们会忽视威胁,而是意味我们会严守纪律地应对威胁。当我们派军参战时,我们会带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去做...我们(美国)出拳时会很小心,但是只要一出拳,就是重拳出击,而我们将果断出拳。”
四、核武器是生存的关键?
在6月25日召开的俄亥俄州共和党晚宴上,万斯以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为例,更精炼地概括了“特朗普主义”(The Trump Doctrine)的核心外交原则,这一原则可以概括为:必要时动武,打完秒撤军。根据NBC报道,万斯在现场明确指出:“所谓的‘特朗普主义’,其实很简单。
第一,要清楚表达美国的利益,这次的重点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第二,要强势地透过外交方式处理问题。 第三,当外交不管用了,那就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解决,然后赶快撤出,别让事情演变成一场长期战争。这就是‘特朗普主义’。
美国的这种战略转型已经也必将对核武器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一个拥核国家可以随时随地威胁甚至侵略一个无核国家的时候,那么防止核扩散变得无效;当美国的“核保护伞”不再有效的时候,那么各国就会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
万斯的这些论述尽管简单,但被普遍认为是美国“80后”这一代未来领导人对美国战略转型的最清晰的表述。但这一战略的本质是其“毁灭性”。就是说,美国不会以常规的形式卷入战争,而是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卷入战争。
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局面。特朗普早些时候公开质疑北约的价值,切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并考虑从韩国撤军,这些举措都在快速动摇美国的安全承诺。而乌克兰战争和伊朗局势正促使世界各国思考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是否才是生存的关键。
伊朗的邻国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在土耳其,电视评论员和部分民族主义政客已经开始呼吁发展本国的核武器,以对抗以色列。
伊朗目前的遭遇也在影响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尤其是韩国。即使在拜登时期,日本和韩国就开始在讨论和美国“核共享”了。今天的情况在迅速恶化。韩国在重新思考是否应当发展核武。民调显示,大多数韩国人认为美国的安全承诺并不可靠,约四分之三的韩国人支持国家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一些专家认为,韩国国内对核武的支持已“进入主流中心地带”,甚至不再局限于保守派,连新当选总统李在明领导下的中左翼阵营也对核选项持开放态度。
过去,积极寻求核武器的多是一些受到西方威胁的国家,例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但今天,在认真考虑这一选项的国家包括了韩国、日本、波兰、德国、土耳其等美国传统盟友。
这并不难理解,在一个越来越危险的世界,各国都必须求自保。不管怎么说,谁也不想“死神”降临到自己头上。
但更为危险的一个趋势是,人类在发展核武器技术方面的能力在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对应对核武器的手段越来越弱化。一方面,随着核技术知识的推广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离拥核越来越近。另一方面,除了人们对拥核或者使用核武器进行一些几乎是毫无用处的道德化的批评之外,还没有找到其它任何办法。如前所述,即使是美国那样的打击他国核设施的方法,不仅无效,反而在刺激着更多的国家发展核武器。
可以预见,随着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人们迄今所见的所谓的“国际社会”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全球化程度大大减低的同时,国家主权得到强化。全球化表明主权国家必须弱化一部分传统的国家主权,尤其在经济面。同时,受全球化的压力,很多国家都会选择加入全球化,因为如果不加入全球化,那么本国就会落后,就会“挨打”。但如果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主权性必然得到强化。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变化至关重要。随着“去全球化”,美国变为相对孤立状态。特朗普政府在加快收紧移民政策,驱逐非法移民,专注于国内的复兴。至少在“MAGA运动”看来,美国地大物博,并且大量的资源未被开采,一个相对孤立的美国能够保持长时期的繁荣。
今天人们所见的“国际社会”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而形成和发展。但如果目前的趋势不能得到逆转,那么在可见的未来,现在人们所见的“国际社会”会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近代之前的帝国时代。尽管因为资本的流动本性,各国不会演变成为远古时代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但国家之间的交往会变得异常肤浅。
不过,人们也无需过于悲观。如果国家之间不能有效交往,那么发展就会成为问题。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普遍真理。这一真理又会迫使国家趋向开放。
不管如何,这是一个新世界,也是一个旧世界。
GBA 新传媒